
文中所有图片均来自《方块皇后》(Queen of Diamonds,尼娜·门克斯执导,1991年)
在近几年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所有女性电影人中,尼娜·门克斯(Nina Menkes)可能是可供人再度发掘的最成熟的一位。她的电影作品规模虽小但至关重要——包括五部长片、两部短片和一部联合导演的纪录片,而这些电影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间被断断续续地制作出来——在对暴力、权力动态和女性心理内部运作的强烈关注方面,她的电影仍然保持惊人地新鲜且几乎无人可比。门克斯1991年的长片作品《方块皇后》最近由(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电影资料馆和电影基金会修复,而此片也许仍是进入她的界限模糊但惊人全面的电影作品履历的最佳切入点。影片由她的姐姐,经常担任她影片主角的丁卡·门克斯(Tinka Menkes)饰演菲尔德斯,一位漂泊在拉斯维加斯、与人疏远的二十一点荷官。影片以一种看似复杂、隐晦的方式展开,与其对一切都不抱幻想的主人公相得益彰。漫长、静止的构图与影片行进中产生的张力相得益彰,菲尔德斯则在片中严肃穿行于城市各个不那么迷人的角落。她的存在是种令人麻木的日常和周围环境所带来的焦虑的化身:在赌场的无数个夜晚,在汽车旅馆房间照顾一位生病老人的午后,以及从邻居的公寓里不断传出家暴的声音。(与此同时,主角自己的丈夫却神秘地缺席了。)门克斯将这些反复出现的故事线索穿插在梦幻般的段落中,而这些段落就像是菲尔德斯令人忧虑的心理活动的生动投射——她由此斯构建了一串图像和情绪的时间流,而即使近三十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也没有失去任何美感或深入其核心的神秘感。
(2019年)4月26日,在全新修复版《方块皇后》于纽约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上映之前,我和门克斯谈到了这部电影长久存在且令人意外的影响,她独自编写剧本的过程,在父权制电影范式之外的工作,她与丁卡的六次合作,以及她在做的巡回视听演讲:“性与权力:压迫行为的视觉语言”。
几年前你跟我提过,你的很多电影都极需修复。而在其他方面,观看修复版的《方块皇后》真正强调出了这部影片的色彩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各种深浅不一的蓝色。与你的其他一些电影相比,在修复工作开始之前,《方块皇后》的胶片劣化和/或损坏程度如何?
2017年,我应邀在德国柏林电影电视学院(DFFB)成立50周年之际,在柏林放映《方块皇后》。而我在介绍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发现,这部电影对于一些电影人来说非常有影响力,这令我非常惊讶:他们被大致统称为柏林学派,比如尼古拉斯· 瓦克巴斯(Nicolas Wackerbarth)和安格拉·夏娜莱克(Angela Schanelec)。我说我非常惊讶,是因为我实际上感觉到我的电影,就像我们放映的35mm拷贝一样,已经从电影意识中淡出。拷贝的色彩缺乏原始版本那种明亮的强度。光学原声带也因为多次放映而被刮花,状况不是很好,而且整体的锐度减弱了很多。
我所有作品的旧胶片拷贝都是这样,但无论是《方块皇后》还是《染血的孩子》(The Bloody Child,1996),都需要原始的画质状态才能被充分欣赏。这是因为这两部作品都使用了很多“长”镜头——镜头时长很长,拍摄距离也很远——所以为了体验影像的细节以及丁卡重要而微妙的表演,做出修复版本非常重要。原声带也非常精妙和层层细分,而在旧拷贝上声音则变得模糊,失去了重要的细节。
我之前没把柏林学派和你的电影联系起来过,但我显然可以看到你的影响力或许会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尤其是在许多那派电影人隐晦的叙事方式中。我知道你看了很多新电影:你在当代电影中有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吗?一些评论家比较了《双峰》第三季(Twin Peaks:The Return)和你的作品,而我认为《方块皇后》是一个由此得出的恰当推论,不仅因为两部作品共同的拉斯维加斯背景,还因为你拍摄景观的方式,以及多数情况下把你的故事设定在城市郊区的做法。
从存在主义的意义上来说,我想我的电影主要存在于当代电影的边缘地带。被和《双峰 第三季》比较我很荣幸,尤其是剧集的第八集: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阴间”世界,电影感丰富而狂野,以无意识的梦境逻辑运作,我认为我的电影也是如此——尽管我的电影更极简。我从很多方面都很喜欢大卫·林奇(David Lynch)的作品,但是他对待女性的方式并不像他作品的其他部分那样具有实验性。我们从林奇作品中看到的仍是对被性化的女人的传统描绘,以及常见的对男性施虐者立场的同情。
因此,虽然我的电影来自同一类内在梦幻核心,但它们深受我作为被边缘化的女性经历的影响:我在多个层面上都是局外人,尤其是在我在电影中体验时间和空间要素的这个方面。与林奇不同的是,我作为一位电影人进入的梦的地带,都不可避免地充满政治色彩,因为我的人生观几乎在各个层面上都反对父权制规范:无论是情感上、精神上还是电影上。
我母亲一家来自柏林,在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全家就逃离了希特勒的统治,重新定居耶路撒冷。我的父亲出生在维也纳——他的家人被纳粹驱逐并用毒气毒死;1940年,他获救并被带到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多年后,当我在维也纳举办回顾展时,白天我独自上街闲逛,却不知为何感到极度崩溃。在一次放映中,我被问到我的女性角色所表现出来的令人痛苦的脱节断联感时,我回答说,这是我作为位女性在一个完全不友好的男性世界中的疏离。策展人威尔伯格·布莱宁-多能伯格(Wilbirg Brainin-Donnenberg)后来问我是不是没觉得这和我的家族与纳粹的暴行史有关。我吓了一跳。我在那之前从没想到过这个。但她是对的。
现在我们显然已经确定,我们会通过DNA代际传递创伤体验——这确实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因此,大屠杀个人史和强烈的女权主义意识的结合,使我与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作品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晰。
我很喜欢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天涯沦落女》(Sans toit ni loi)。我第一次观看时,我完全感同身受,觉得几乎可以自己拍出这部电影!主角莫娜完全拒绝与“体制”合作,这让我深有感触:她最终死在了一条沟里。我对此的理解难以言表。
我也喜欢阿莉切·罗尔瓦赫尔(Alice Rohrwacher)的《奇迹》(Le meraviglie)——她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如此流畅,而且她让现实世界自然地成为了想象的一部分。她将可见与不可见的东西联系了起来。我也是这样看待我的作品的,当然她的视觉风格和基调非常不同。
去年十一月,我在AFI电影节上观看了《方块皇后》的修复版本,我被这部电影的当代感所震撼:你要说它是去年拍摄的都没问题。但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和多数当代电影有亲近感。

说到《方块皇后》的当代感,我想知道这部电影在你拍摄后的这些年里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变化?回看过去,你对这部电影的概念——无论是在拍摄之前还是之后的几年——和你现在看到的有什么不同吗?你认为现在其他人第一次观看和最初那批观众有不同的看法吗?这部电影以一种看似复杂和神秘的方式发展其主题和处理时间,这种方式甚至不同于你之前的长片《马格达勒纳维拉加》(Magdalena Viraga,1986)。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觉得《方块皇后》处于什么位置?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之外,我的电影其实形成了一个连续统一体,密切追踪着我自己内在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以我姐姐女演员丁卡的形象体现了很多年。《方块皇后》是我们合作的第四部电影,它表达了一种比《马格达勒纳维拉加》更为极端的疏离感。我在片中很多地方都看到了这种更深层次的疏离感:比如影片非常缺乏特写镜头,比如影片17分钟噩梦般的二十一点发牌段落——这段对我来说,仿佛是主角被困在地狱的景象中——再比如丁卡的角色菲尔德斯会在每个场景中都出现,但同时又保留了她作为背景人物的特质。
我将我的主角命名为菲尔德斯,这是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天堂”,以纪念纳瓦勒·萨达维(نوال السعداوى)小说《零点女人》(امرأة عند نقطة الصفر)中的女主人公。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埃及妓女杀死了她的皮条客并拒绝表达悔意的故事,尽管这样做可以使她免于死刑。《方块皇后》中的菲尔德斯和《马格达勒纳维拉加》中的伊达没什么不同,她们的确都是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且与外界断联,但前者还有一种怪异的力量,也许是由于她内心坚定不移地拒绝崇拜伪神而产生的。是菲尔德斯/丁卡让棕榈树在沙漠中燃烧,或让一个倒立耶稣出现在街头的吗?她对体制的排斥是否足以使其垮台,或者至少造成一条裂痕?
我觉得现在人们对这部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影片有了一种奇怪的新鲜感——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尽管它拍摄于很久以前,这些都证明了丁卡/菲尔德斯精神力量的真实性,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我这里,这部电影是通过出于直觉把注意力集中于内心,而没有去顾及外部电影规范而拍摄的。我试图融入我自己内心最深层的关于这部影片所讲述的政治/情绪情景,然后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比方说,发牌场景必须做成长段落,这种感觉就像一种事实和一道命令。这个决定实际上出现在剪辑过程中:有五六段不同的发牌场景,最终形成一段单一的极其长的段落,而它们最初是作为独立分散的事件写在剧本里的。尽管我非常担忧多数观众会在赌场场景中离场,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处理手法。而且我想感谢丁卡以这样的想法来剪辑这部电影。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我的电影处理时间的方式可能是它们最大的优点之一!社会力量不仅决定了谁能赚钱,谁不能,谁是中心,谁是边缘,而且还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空间和时间。我同意《方块皇后》的时间观比《马格达勒纳维拉加》更不寻常,但我们后一部电影《染血的孩子》,其结构更加极端。
我不确定《方块皇后》该放在我“职业生涯”的什么位置,因为对我来说,我做电影从来不像是一种职业,而更像是一种使命。虽然使命有时也可以是一种职业,但它整体上看还是一种使命,而如果这作为职业生涯获得了成功,那就是非常幸运的奇迹和意料之外的副作用了。
我的每部电影都是在极低极低的预算下制作的,我从来没有真正从我的电影中赚到过钱。对于《方块皇后》,我的预算大约是50,000美元(约合36万人民币),其中一半用于35mm胶片和洗印。我们花了几百个小时打电话寻求捐赠,从摄影机套装到咖啡,再到拉斯维加斯的免费酒店住宿。但随着《方块皇后》的修复,如果这部电影,以及我的整体工作获得了新的、更广泛的认可,也许(获利)是有可能的……谁知道呢?我有两个长片剧本,非常想拍出来;我很希望能生平第一次获得充裕的预算。
你能描述一下《方块皇后》的剧本写作过程吗?你写这部剧本的方法和你写以前的作品的剧本有什么不同吗?这部电影给人的感觉特别像是一系列精心组织和结构化的场景,以至于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从剧本较长的段落中删减下来的。而且,也许巧合的是,这也是你最短的一部长片。这部电影的许多省略部分是在剪辑中实现的,还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写的?
整部电影都是按照一个非常精确的剧本一字不差地拍摄完成的。没有一个场景被缩短,虽然赌场的场景,当然如前所述被加长了。那些看似随机的场景,或者像纪录片一样的场景,比如大象鼻子摇摆,或者婚礼场景,甚至是棕榈树燃烧的场景,都是精心构建的。
除了极长的发牌场景,电影的剪辑几乎和剧本一模一样。我还写过一个场景,但最终被剪掉了:一个性感的裸体女人,躺在沙滩上,身上盖着小贝壳——不知道她是死了被冲上了岸,还是某位沉睡的海神。这个女人应该出现在影片最后,快到婚礼场景的地方。但最终,那些画面感觉还是不合适。
我想,我的剧本写作方法正是一种从传统编剧体系的倒退!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好几个月,也可能是一年,甚至更久——我一直在做的是,在3×5的卡片上写下影像:要么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东西,要么是我脑海中出现的内心图像:“一棵燃烧的棕榈树”、“在赌场外的汽车里自杀”、“庄家在赌场里工作”等等。有时我的梦中会出现一些画面,比如倒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写下那些具有强大能量并吸引我注意力的图像。所以当我有了一堆这样的卡片之后,我就有了一种感觉:在某一时刻,我已具备了足够的出于直觉的闭环感。然后我就开始阅读所有的卡片,看看其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叙事线索,然后我开始把这些图像串在一起,写成剧本。因此,尽管在更标准的剧本创作中,故事是最先出现的,随后再添加图像,但我的体系是利用图像将我引向未知的叙事或半叙事的目的地。

你能谈谈你和丁卡的合作吗?我觉得她是一个迷人的人物,也是你第一阶段电影制作的核心——她是如此令人难忘和引人注目的存在——但据我所知,她从未在其他任何电影中出演过。我知道她在你的其他一些影片中负责过不同的工作——比如她参与了《染血的孩子》的剪辑工作等等——但总体来说,她在创作,甚至是编写她那些角色的过程中的参与度如何,尤其是在饰演菲尔德斯时?
丁卡和我一起拍了五部电影(《A Soft Warrior》,1981;《佐哈拉的巨大悲伤》,1983;《马格达勒纳·维拉加》《方块皇后》以及《染血的孩子》)。在所有这些影片的创作中,她的参与既是必要的,也是革命性的。丁卡实际上并没有和我一起编写任何东西——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我的编剧过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非常安静和私密的,但对于那些没有任何剧本的电影,比如《染血的孩子》,丁卡就在内容和结构上都贡献了核心灵感。但即使是在按剧本非常精确地拍摄的电影中,比如《马格达勒纳·维拉加》和《方块皇后》,丁卡也给片场带来了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充满带电一般的能量。
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在片场安放这么一个人——即你的主角——同时明白/感觉到她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着深刻的、内心的理解,无论是在单个场景的微观层面上,还是在整部电影的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一点也不符合传统,所以拍摄每一部(我们的)电影就像是一次神秘而有力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险。在较隐蔽的层面上,丁卡总是凭直觉比我更了解电影中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且她很勇敢。她以一种非常微妙但非常强烈的方式,把事情推向极致。在拍摄时我能感觉到这一点:那给了我勇气,使我自由,从而让我做到最好。
表演方面,在《方块皇后》中,此前我脑海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一位二十一点游戏的女发牌人,她是位流浪者,孤身一人。但丁卡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形象,使其达到一种超然境界:在那里,我们文化中对女性的深刻伤害与美国的暴力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我没法解释这个。我们有一种心灵感应式的互相理解,所以除了调度,我不需要做太多很刻意的导演工作。她总是把事情推得比我想象的更深入,而之后在后期制作中,她的剪辑见解独特而激进——她的想法从来不关于风格本身,而在于从形式上、结构上揭示电影的核心意义。
由于丁卡至今仍在与一种使人衰弱、危及生命的生理疾病作斗争,我们的电影合作在我们完成《染血的孩子》之后就结束了。
你在2018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发表了一次题为《性与权力:压迫行为的视觉语言》的演讲。这个演讲最初是由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丑闻引发的,但显然几十年来你一直在研究这些想法以及它们与电影的关系。你能描述一下这些想法最初是如何合成为一次视听演示的吗?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你的演讲有什么进步发展吗?你有没有继续在演示中添加影片或示例?
我一直对政治性共鸣、镜头内涵和叙事结构有着一种直觉。
事实上,我必须自己拍摄所有电影的原因是,只有通过摄影机镜头,我才能理解和感受到我自己的电影。如果我站在一边,让别人帮我取景和拍摄镜头,我会感到孤立和迷失。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南加州大学教电影制作课程时,玛莎·金德(Marsha Kinder)邀请我和她一起共同教授一门批判性研究课程:《性别与电影》。我是我们教学团队负责拍摄的人,玛莎则提供了理论基础。那是我第一次读到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和其他女权主义理论家理论的地方。那很棒,因为它给了我一种语言,让我能够清晰表达我一直以来的感受。2017年初,当电影人尼古拉斯·瓦克巴斯邀请我参加前文提过的德国柏林电影电视学院庆祝活动时,我第一次在柏林公开发表了我的演讲。但自从和玛莎·金德一起教过课后,我一直在向我的学生们展示我的“性与权力”演讲的不同版本:用一系列来自一线导演的片段,揭示了镜头设计是如何从形式上削弱银幕女性力量的。
(我得到的)反应总是震惊、沮丧,甚至是恐惧。但至少我大多数女学生的日常感受就是这样。带性别偏见的镜头设计:角度、布光、构图和运镜已经变成一种规范,以至于我们习以为常,而当所有这些都进入个人意识时,它可能会带来很难熬的体验。所以,2017年10月,当韦恩斯坦的事在《纽约时报》上曝光时,我决定写一篇论文,探讨电影的形式语言如何成为#MeToo和#TimesUp运动所提问题的一大因果因素,甚至可以被称为强奸文化的基石。让我吃惊的是,这篇文章在Facebook上疯传,后来被《Filmmaker》杂志评为本年度最受欢迎文章!忽然间,越来越多的人对我的演讲感兴趣;这不再被认为是晦涩的电影理论,而是直接关乎我们的当代日常生活经历。作为女性,我们每天都被边缘化,被物化,成为我们生活中和银幕上的物品——而这经常出现在那些获得奥斯卡奖或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的电影中。
我最近添加了一些片段,展示了一些针对女性的镜头设计策略是如何被用于其他边缘群体的,比如跨性别人物——所以,没错,这个演讲绝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整体。我也很高兴《性与权力》现在正在被拍成一部纪录长片,临时片名为《洗脑》(Brainwashed),由Uncommon Productions公司的蒂姆·迪士尼(Tim Disney)和Marginalia Pictures公司的伊丽莎白·本特利(Elisabeth Bentley)制片。这能让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探讨的重要信息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甚至可能对在职电影制作者及更广泛的集体意识产生真正的有意义的影响。

你提到了两个你想拍的剧本。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些项目的情况,以及这些年来你在融资和寻求支持以创作新作品方面遇到了哪些障碍吗?我有留意你早期长片演职员表中列出的所有拨款和资助方。在本世纪头十年,筹措资金比现在难度大多少?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你作品的文章提到了一部名为《Heatstroke》的电影,但这部电影显然没能拍成。
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话题!我喜欢电影制作的各个层面,除了融资部分——这部分几乎总是令人筋疲力尽,感觉无比困难。当女导演并没让事情变得容易。当我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的学生时,我利用周末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马格达勒纳·维拉加》。这部电影获得了1986年洛杉矶电影评论家协会最佳独立/实验电影奖,当时我们既震惊又激动。这部电影也入选了多伦多惠特尼双年展。换句话说,这部电影得到了很多关注!但这并没有引起好莱坞有钱人的兴趣。准确地说,没人出价要买。
我的电影很早就得到了一些电影评论家和影迷的赞赏,而且我可能接受过几乎所有形式的公共支持——来自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古根海姆、洛克菲勒、西部各州地区媒体艺术奖金、创意资本等等。但是,尽管所有这些奖项都很有声望且深受赞赏,但它们并不会带来很多实际的现金。我所有的电影,都是用微薄的预算制作的,甚至连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而它们现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强烈、迫切的需要:即不惜一切代价、毫不妥协地完成我的电影。
我看到男性同行拍摄了受到好评的第一部电影后,会接着在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电影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但对于女性导演来说,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且仍然很少发生。我自己是位女性是其中的一部分要素,但我的电影内容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激烈了。比方说,《马格达勒纳·维拉加》是关于一个厌恶自己工作的风尘女的故事。她愤怒、疏离,从不脱掉衣服。因此,根据我在《性与权力》中的演讲,我违背了电影中性别的基本法则,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另一方面,我的创作原则完好无损。
在完成《染血的孩子》后不久,我写了《Heatstroke》的初稿,这是一部关于在洛杉矶和开罗的两姐妹的政治惊悚片。《Heatstroke》是埃舍尔(Escher)式的心理创伤探索,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破碎背景下展开。正如你提到的,这个项目是几年前由Muse Productions公司的克里斯· 汉利(Chris Hanley)牵头的,但在融资方面遇到了一些障碍。不过好消息是,《Heatstroke》获选了2019年戛纳电影节新女性电影推销单元“突破镜头”。我会和我的制片人伊丽莎白· 本特利一起飞过去寻找并完成融资。本特利将以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电影《隐秘的生活》(A Hidden Life)制片人的身份出席电影节,该片在主竞赛单元首映。我相信,我们的联合力量,加上对女性如何被系统排除在“正典”之外的认知,意味着《Heatstroke》终于可以被拍出来了。
我想拍的第二部长片剧本是《Minotaur Rex》,部分由格温·韦恩(Gwen Wynne)和EOS世界基金会制作。《Minotaur Rex》是基于希腊弥诺陶洛斯神话的剧情惊悚片,只是故事发生在当代耶路撒冷。这个故事既是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种族主义压迫的政治状况的寓言,也是关于一个愿意面对并与自己的阴暗面搏斗的人的内心历程。我所有的电影最终都是关于面对自我的旅程,这是我个人最致力于展现的关于人生的一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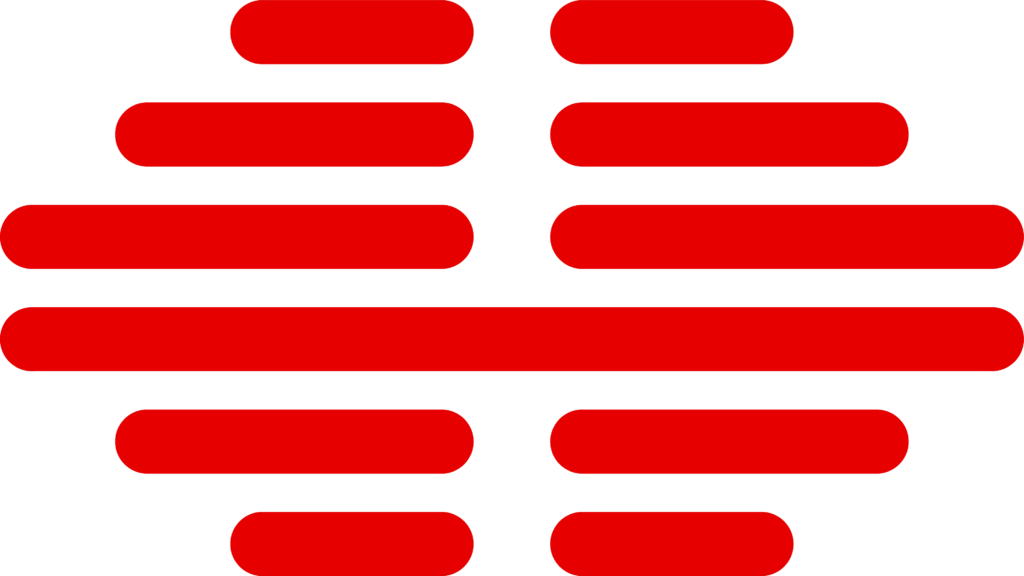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Jordan Cronk | Film Comment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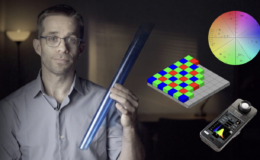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