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IMDb
霍尔·哈特利(Hal Hartley)是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和作曲家。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独立电影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最著名的电影作品是《难以置信的事实》《信任》《小人物狂想曲》《业余爱好者》和《傻子亨利》,这些电影以冷幽默和在对话中引用哲学的古怪角色而著称。哈特利经常使用他的笔名奈德·来福(Ned Rifle)为自己的电影配乐。自1988年以来,他编剧、制片和执导了14部电影长片,全部获国际发行。除了在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各种奖项之外,他还编排过戏剧和歌剧项目,且目前经营着自己的公司——Possible Films公司。

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和作曲家。
本文中,电影制作者霍尔·哈特利讲述了如何管控制作手段,适应环境,以及管理维护好自己的作品存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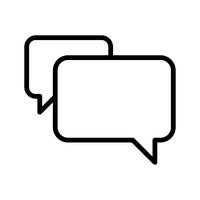
你正在做一个Kickstarter项目,内容包括建立一些你早期电影的存档。回到这些电影的世界,并能够悉心打理自己的作品和存档,这种体验作为一种创意操练的感觉如何?
我很感激有这么多作品我可以,首先,加以回顾,并感觉良好;其次,我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点一点做了必要的事,即确保我对这些东西有所有权,我可以控制它们,或者我最终可以把它们拿回自己手里。多年来,看到发行商没有真正为电影做出正确决策,这多次让人感到失望。粉丝们会在我的网站上留言:“为什么我在西班牙看不到《招蜂引蝶》(Flirt)或《业余爱好者》(Amateur)?”于是我会查看记录,看到我确实在那有个发行商,然后我会写信给那些粉丝,让他们知道实际上能在那看到这些电影,并把发行商的公司名称告诉他们。然后粉丝们会回复我说:“好的,但是能看到的方式只有很烂的DVD,设计糟糕,制作也很廉价。”所以,在我拍摄不同电影时,我一直有在留意我签的各种合同的有效期,但直到2015年左右,我才意识到我很多电影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版权都回到了我自己手里,只是它们会分批回归。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按照我拍摄的顺序发行它们,因为我必须等到发行权到期。我只能等待。
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把这些早年的电影作品放在一起,可以做成一个不错的合集。我们现在就像一家设计公司。针对这个项目我们有三部电影,一些短片,一些小型纪录片。我们把它们放到一起,然后花了很多时间设计盒装包装和CD,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以配合这个合集。
有趣的是,很多电影制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艺术家通常都不是自己作品档案的良好管理者。
是的。我有我自己内心的“图书管理员”。我从小就这样。如果我制作了什么东西,我会想清楚它在哪里,保护好它,并留有一个我自己的拷贝。我最近很高兴看到了亚历克斯·温特(Alex Winter)关于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的纪录片。扎帕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人,但我之前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也是我这样(的档案管理者)。我是说,他把所有东西都存档了,体量超级大。他对此非常小心仔细,差不多也(和我)做了同样的事。在他30多岁的某个时候,他明白过来:如果他自己处理所有的工作,他可能会做得更好——自己制作,自己发行,自己推广——而他也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仔细察看你的早期作品有没有让你思考你的流程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改变?或者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当时做出的某些选择现在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与创作材料的关系不一定会改变,但我确实看到了我的工作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份档案包括三部电影——《业余爱好者》《招蜂引蝶》和《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是在2012年制作的,所以它大致比《业余爱好者》和《招蜂引蝶》晚了10年。和前两部一样,它是我认为的我的“城市”电影之一,但它的制作成本要低得多,工作人员也要少得多。看我如何编排画面,用一点点动作,一点点对话做成一部电影,这非常有趣。比方说,在早期作品中,我会用一台dolly车移动摄影机,而在规模较小的影片中,我通常不用dolly车。这是一部低成本电影和一部超低成本电影显著不同的特征。我现在会看出一些创作策略,它们基于同样的构图基本原则,保持画面鲜活,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一种类型的镜头变成另一种类型的镜头,而你可以通过移动摄影机或移动画面中的个人或两者兼而有之来实现这一点。
这就是你所采用的那种电影构图语言,而且我很高兴看到它保持了前后一致,无论我是在制作一部小小的视频电影,一部在一两个助手的帮助下我自己在摄影机前录的五分钟视频,还是一部剧组有30人的影片——在我查看和构图的方式上有种真正的一致性。
谈到电影制作几乎总会谈到它的商业性质——即人们如何筹集资金,以及片子怎么筹款。
这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九十年代相比,即使是现在的独立电影,概念也已经截然不同。我很好奇你是如何适应这些变化的,或者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你思考的方式或你的艺术创作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甚至是在我了解这个行业之前,在我开始专业拍摄“电影”之前,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一切就已经开始了。我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思考,而我现在仍然以这种方式思考。我想说,你该尽可能多地控制自己作品的制作过程,因为如果少一些他人影响,少一些外部因素(其中一些是错的),作品会更好。
渐渐地,我成为了一名专业人士,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一步步做出决定。也许某位投资人希望在剧本阶段有所更改,我就不得不考虑这一点。多数时候我会保持变通,但我确实因为对创作有点强硬而出名。我会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最终我会根据自己的品味和感觉做出决定——在剪辑阶段,以及在我与发行商、营销人员和宣发人员打交道方面,都是如此。我觉得我有点比较难搞的名声,但我对此还蛮高兴,因为我现在仍然在做这行就得归功于此。我通过打理这些电影来养活我自己和公司。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只从商业角度看待电影,这些电影只会悄无声息地烂在什么地方。
这真的有点伤我的心,比方说,我的其中一部电影,《终止不幸》(No Such Thing),我当时是为一家制片厂拍的。那是我唯一一次被说服加入项目。现实是,他们会给你一大笔钱,而你永远无法控制这部电影,但我选择信任各种参与其中的组织。结果最后,他们什么都没做,这部电影就这么被束之高阁。我记得它好像在什么地方出过DVD,但这事他们做得非常差劲。所以,回到扎帕的话题,我从小到大不仅听他的音乐,还听他谈论他如何经营他的生意和管理他的档案。所以那种(做好自我管理的)心态一直和我非常贴近。
现在所有东西的商业模式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变化,所以看起来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你越能真正拥有整个创作过程的所有部分,产出也就越能有利于你。
没错。当然这会有短期的挫折。你可能会错过这门生意中很多真正赚钱的部分。我现在很难说服那些制作电视节目或流媒体节目的公司认真对待我,因为他们还很年轻,一直专注于主流娱乐节目,而我不属于那一类。他们和我的经纪人或者经理人谈话时,会说:“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他是90年代的大人物?”很难让他们对我感到兴奋,即使他们可能对我提出的故事点子感到兴奋。他们以一种完全集团经营的方式工作。
比方说,我告诉他们:“我已写完了整个剧集。”他们读了试播集剧本,非常喜欢,也喜欢整个创意,然后他们提出建议:“我们会为你安排一整个编剧团队。”我说,我不需要一个编剧团队。剧本都写好了。都搞定了。已经万事俱备了。”他们会说:”噢,不。我们不那样工作。那不是我们的工作方式。”于是我说:“那好吧。”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特定的挑战和困难。我认识一些需要处理这类问题的音乐家,还有视觉艺术家。如今给这行所有人的一个普遍建议就是最好自己动手。如果你能用iPhone拍电影,那就去拍吧。最好自己去做,这在某些方面非常正确,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是啊,还有,这会是一部好电影吗?这也仅仅是简单地用你自己想要什么来定义什么是“好”,而即使是个拥有iPhone的孩子也可能只是在他的脑内或心里有一部电影的想法,但没法用手机拍出来。也许他会需要一位剧组工作人员,也许还需要更有经验的摄影师,所以,没错,这是种平衡。不过这的确是事实:如果你是个创作者,无论何时你都得看看你的资源和你的目标,你必须调整好两者的关系。
几年前我也做过同样的事。我筹集了大约30万美元(约合218万人民币)打算拍一部叫做《Where to Land》的电影,就在疫情爆发之前。最后我们不得不把钱还给所有人,因为我在疫情期间拍不了这个片。我本来可以用30万美元把那部电影拍得很不错的,但要在防疫协议的约束下工作,我真的需要近100万美元(约728万人民币)才能做到,而我没有100万美元,我也不认为我可以靠自己筹集到100万美元,所以我决定,我现在就不拍那部电影。
这很难。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况:我可以做这个,但也许这并不会是我真正想要的结果,而且即使做了也总会让我觉得有所妥协,那也许我最好还是别做这个。你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你是让这个想法暂时退居次席,觉得之后还会回过头来再想想,还是比较像那种,过去了的就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该想想别的事情了?
我不会放弃。我会暂时把它放在次要位置,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已经拍这样的片子拍了差不多……35年了?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个。我只是想用正确的方式拍。我不想在制作过程中处处妥协敷衍,最后以一种学生电影的心态拍完整个影片,不过这种事在我的职业生涯早期就存在。我记得1992年在《小人物狂想曲》中,我和英国的投资公司谈,他们对剧本非常感兴趣。但他们希望在剧本中做出某些类型的更改。我觉得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他们只是想施展自己的企业影响力,他们得向上级表明,他们提了意见,而电影制作者听取了意见,结果我就没法合作。都是些很蠢的意见。尽管在此之外他们人很好,也很聪明,但提的都是些愚蠢意见,于是我说:“这样吧,我们现在谈的是部要花250万美元(约合1820万人民币)的电影。如果我不做这些更改,而你们只给我200万美元(约合1456万人民币)怎么样?省了50万美元。”然后他们答应了。他们说:”当然。行啊。好的吧。”
我想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每一个行业,每一种艺术形式里——有些人想随意改变创作,只为了能借此说明他们已以某种方式证明了自己工作的必要性。
是的,但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候,这只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品味和感受,以及对手头作品的误读。
你用Kickstarter给很多项目筹了钱。有时候众筹会给人一种势利感,但我其实不太明白。比方说,我曾和一位电影制作者谈过,他正在考虑为他的电影做一次Kickstarter众筹。他担心的是,如果他的项目是众筹筹到的钱,他就不会被认真对待。
一开始我不得不忍受很多这样的事。“势利”可能甚至不是最合适的词,但这是一种真正的、根本性的资本主义心态:如果你没有以他们所认为的合法的方式得到钱,他们就不会尊重你,因为他们会认为这等于是一些不法之徒通过一些无法接受的商业活动偷了钱,然后他们把这钱投资在你的电影上。而这却是合法生意。此外,许多真正的资本家会很高兴地去看,比如说,马克·莫里斯舞团(Mark Morris Dance Company)或类似的东西,这类团体主要由企业资助,但也有政府补贴。如果没有大量欧盟和国家政府对艺术的补贴,我不知道眼下欧洲还有哪个电影制作者能够真正有活儿干。
在美国我们没有那套机制,所以你得换个角度思考。在Kickstarter引起我的注意之前,我已经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很多年了,而等我搞明白了Kickstarter,我觉得:“没错。这正是我一直在想的东西。”我在2004年制作了一部电影叫《星期一女孩》(The Girl From Monday),而当时我和我的创意团队的想法是:“咱们来完全靠自己制作一部小型电影,然后建一个网站,人们就去那里看这部电影。他们付比方说99美分(约合7元人民币)就能看到这部电影”
在2004年,相应的互联网技术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采用了更传统的电影发行方式,但是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到一种直接面向影迷,绕过所有公司机构、发行商和销售代理机构等等的发行方式。2011年,我第一次在Kickstarter上为一部新电影众筹。效果很好,我也理解那套机制。在第一个项目顺利完成后,我苦思冥想,开始构思一套计划来建立自己的观众基础,扩大已有的观众基础,协助制作项目,同时推广自己的作品——基本就是做预售。
举个例子:图书出版商已经这样做了150年。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书都是预售的,所以我也是这么构想的。所以,没错,一开始你得忍受很多可鄙的事,但一步步地,你的电影作品问世了,而这是一门真正的生意。从2016年左右开始,我每年都会用Kickstarter做一次众筹,这也是我们发行我作品相关业务的基础。
我认识的很多电影制作者都会有一些明显的高产期:这种时期你实际上是真正在脚踏实地地拍电影,人就在摄影机后,但接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则不是这样——你可能是在做电影相关的其他工作,或者你正在做与你未来可能拍摄的电影相关的工作——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时间里,你觉得做些其他种类的创意工作重要吗?比如在你没有真正着手做自己的老本行的时候,这些东西能强化你自身,之类的?
我很幸运,我有不同的兴趣,总能让自己忙起来,也对工作充满激情。我很幸运,因为在我职业生涯的开端,一切都非常快地发生了。我当时一直在拍短片,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我拍了第一部长片电影《难以置信的事实》,而它成功了。那是在1989年。基本上,十年来,我的工作并没有间断。人们疯狂地给我投资。这是当时电影这个行当中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独立的电影制作方式,让我感到很惊讶。我当时从未听说过“独立电影”这个词,直到我有了我的第一部电影,但是我毫不停歇地工作了十年,在那之后我打算减缓一些步伐。
我那会儿已经结婚了,在经济上也过得不错,所以我当时只是想放松一点,继续工作,但我想以不同的方式工作。那只是恰好发生在利润丰厚的独立电影生意宣告结束的时期罢了。又过了几年,当我想做些新事情的时候,情况变得更困难了。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支持那些不那么明确属于主流的电影作品更难了。我当时有点后悔:“噢,我本来该留一手的。我不该像那样直接离开几年。”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有别的事要做。
我对戏剧制作很感兴趣,而我也去做了。我编排了一出歌剧,创作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音乐,并且在把这部分音乐事业建立起来的同时,还继续在写剧本。我最近还开了家出版公司,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每位创作者都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我总觉得拥有不同的创作出口会比较健康,也有心理价值,所以当你不能做这件事时,你可以暂时转去做其他事。你会发现这些事都在以某种方式互相影响,且通常你自己都没意识到。
是的。对于那些只擅长做单独一件事的人来说,这一定非常令人沮丧。我在电影行业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非常有才华,有时三、四甚至五年都拍不了任何片,因为当时没人对他们想做的片子感兴趣,即使他们已经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电影制作者,好的编剧,等等。他们有种外在气质。他们都有种特定的肢体语言。他们经常坐立不安。
你会看到那些对现状充满怨恨的人,你也会看到其他人——后者会说:“好吧,现在的世界和1995年不一样了,所以我只需要弄清楚如何在2021年做我想做的事就行了。”毕竟环境不同了。
我总是向那些音乐人看齐。在音乐人身上更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大卫·鲍伊(David Bowie)就很棒。现在的音乐界有种全新潮流正在发生,痴哈(trip hop)音乐之类的,而对此他就会说:“行,我是个45岁的人,而现在我得开始做这样的音乐来了。”然后他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制作他自己的音乐,来迎合这种新潮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肯定做过10到12次这样的事,直到晚年,他才说:“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和任何潮流都无关。”
我努力追随其他艺术家的例子,看看他们如何变老和改变自己,并让这些自身的改变继续存在,而非压制它们。你得在很多其他方面也有创造性,不仅仅是在你的工作中,你也得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把你的工作推广出去。先思考你打算怎么把作品创作出来,然后再思考它将如何迎合当前的时代精神。这样想没有错。这并不代表你是机会主义者什么的。
尽管如此,许多一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家——从扎帕和鲍伊到其他数百位我钦佩的电影制作者和音乐人——一直寻找着在集团化娱乐世界之外的运作方式。你没有高薪保障,也没有对广泛发行你作品的承诺,但你确实有着更多的创作自由,而你也不必对事物的现状如此生气,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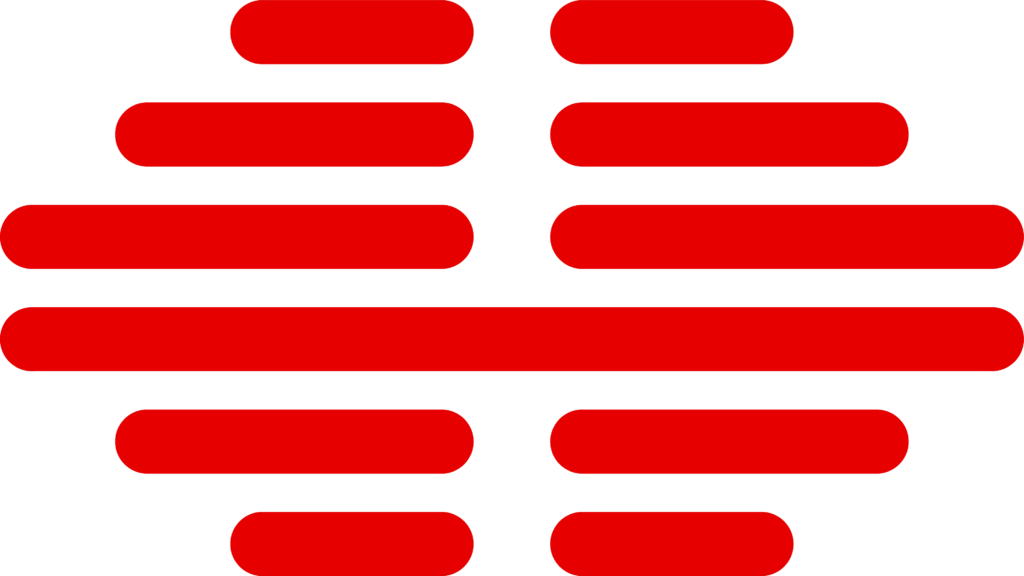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T. Cole Rachel | The Creative Independent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