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Vittorio Zunino Celotto/Getty
头图:2013年5月26日,法国戛纳影节宫,导演是枝裕和正在第6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者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他凭借《如父如子》斩获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日本作者导演是枝裕和日前在戛纳推出了他的最新剧情片《怪物》。本文中,他谈到了这部影片与黑泽明《罗生门》之间的对比,为什么这部电影是对自己的一次背离,并谈到了与已故伟大作曲家坂本龙一的合作。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常喜欢提“戛纳家族”,指的是一大批戛纳电影节协助发掘、培养的国际导演,他们已成为知名影节宫红毯常客。而如今,戛纳的日本人文主义电影制作优秀传统的最佳代表无疑就是是枝裕和——其长片曾七次入选戛纳电影节官方评选,创下了日本电影的纪录。顺带一提,是枝裕和作品的主题也是家庭——破碎家庭,动荡家庭,以及非原生家庭。尽管手法多样且富有创造性,但他在戛纳电影节最出名的作品都围绕这一主题拍摄。
2013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得主《如父如子》讲述了两个男孩婴儿时期被错误调换家庭的故事。多年后,发现了这一事实的两对父母们面临一个痛苦的决定:是把孩子送回去,还是留下这个自己一直抚养到如今的孩子。与此同时观众也能到,影片对日式父亲在“爱与尊重”方面的角色转换进行了一次极其切中要害的深思。2016年,是枝裕和忧郁温柔的剧情片《比海更深》在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首映,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如The Hollywood Reporter的影评人当时所评价的那样,影片是“一部经典日式家庭剧情片,具有温柔的说服力和惊人的简洁性”,但“在温和喜剧和人类真实本性的沉郁现实间达到了完美平衡”。
2018年,和枝裕和携《小偷家族》来到戛纳,而该作立刻被誉为其职业生涯最高峰——电影节评审团也认同一点,授予了是枝裕和金棕榈奖。这是20多年来戛纳电影节首次将最高荣誉授予一位日本导演(此前有过这一成绩的日本导演包括今村昌平,其作品充满社会人类学色彩,曾在1997年和1988年分别凭借《鳗鱼》和《楢山节考》在戛纳二度获奖;伟大的黑泽明凭《影武者》在1980年获奖,而衣笠贞之助则凭借《地狱门》在1954年获奖——这也是第一部在西方上映的日本彩色电影。)
《小偷家族》是一个充满讽刺幽默和不寻常的同情心的故事,讲述了一群小偷小摸的罪犯们收养了一个受虐待的年轻女孩,并短暂组建了一个脆弱的临时家庭的故事。而在去年,是枝裕和携影片《掮客》重返戛纳电影节主竞争单元——他视其为一部与《小偷家族》相关联的作品,同样围绕不合群者聚在一处寻找难以捉摸的慰藉,不过《掮客》是以韩国电影业为主体拍摄的,主演包括独一无二的宋康昊和裴斗娜。影片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天主教人道奖。
眼下,是枝裕和显然非常高产:今年一月,他在Netflix发行了自己第一部剧集《舞伎家的料理人》。今年五月,这位年届六十,举世瞩目,智慧且良善的家长式电影人,带着他的新作《怪物》重返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部作品触及了他的许多标志性主题,同时也开创了新的形式。影片围绕一个名叫凑的男孩展开,他的单亲母亲觉得他的行为开始变得古怪,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发现有位学校老师要为此负责后,她冲进学校,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这个故事分为三个不同的章节——透过母亲、老师和孩子的不同视角——而观众会像观看《罗生门》一样,透过每个角色的眼睛反复观看这个故事,而真相由此逐渐显现。
是枝裕和倾向于自己写作电影剧本,《怪物》是他自虚构长片首作《幻之光》以来第一部由另一位编剧编写剧本的作品。《怪物》由日本著名电视剧《母亲》《女人》和《最完美的离婚》的编剧坂元裕二负责剧本。《小偷家族》的一位突破性主演安藤樱,在片中主演了一位母亲。而于今年三月去世的奥斯卡获奖全才作曲家坂本龙一,则为这部电影写了配乐——这成为了他的遗作。
近期,《The Hollywood Reporter》在是枝裕和位于东京涩谷的办公室与他坐下来讨论了《怪物》的制作和内涵。出于对文章长度和清晰度的考虑,我们对谈话内容进行了编辑。
这是自从《幻之光》(1995)以来,你第一次与编剧合作。在自己写了这么长时间的电影剧本之后,导演别人的剧本是什么感觉?
其实这话我说了很多年了,如果我哪天要执导不是自己写的剧本,那我想合作的编剧肯定就是坂元裕二。这些我都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也在这些年来的很多采访中都这么说过,因为我一直很尊敬他,认为他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伟大编剧。此前他一直和制片人川村元气和山田兼司一起开发这个项目,而当他们找上我的时候,还没等他们告诉我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我就立刻答应了,因为这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次合作。我觉得我们能拍出一些真正有意思的东西,而且我想这部电影会与我之前的作品有些许不同。

图源:2023《怪物》电影制作组
开始这个项目后,你对这个故事本身有什么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从2019年开始合作。两人会定期见面,分享意见,然后坂元先生会回去重写剧本。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三年。从一开始,故事本身就很吸引我。我还觉得它会给我带来一次有趣的挑战,因为它有如此清晰的三章结构。从主题上来说,在这个后疫情时刻,环顾四周,我觉得你会在世界各地看到许多实例:人们会把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当成“怪物”。这就造成了各种分歧和根本性的误解。也许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疫情。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这无疑是一个超前于时代的剧本。当我在眼下这个后疫情时代观察周围的世界时,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现象。我既觉得它很让人困扰,也觉得它很有意思。这部电影实际上有个和现在不一样的工作用临时标题,但在我们讨论的某个节点,我建议我们应该叫它《怪物》。
在像你这种地位的日本电影人拍摄一部采用多视角叙事的电影时,大家几乎不可能不马上想到《罗生门》,而对那部电影的传统解读是它展示了个人视角的不可靠性,以及达成普遍真理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怪物》的前两章给我留下了类似的印象,我们首先从母亲的角度来体验这个故事,然后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同样的事件,同时也从校长的角度收集到了一些信息。但最终在第三幕中,我们以位于故事核心的孩子们的视角看到了一切,而他们似乎揭示了故事的真相和真正的利害攸关的东西。这一切的展开方式,在我看来,就好像你在用《罗生门》的方法来表达成年人是多么难以深入和理解儿童的世界和经历,即使他们带着最善良的意图。这部电影似乎在呼唤一种人文主义价值,而你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关于这种价值的:敏感、耐心和一种非常纯粹的善意。这个问题比较长。你怎么看?
(笑)当这部电影被戛纳选中的消息公布时,蒂耶里·福茂其实就用了《罗生门》这个词来形容它,所以我想会有很多人带着对那部电影的印象来看这部电影。但是,正如你刚才敏锐指出的,当你看到影片的第三章,你可能就会明白,我们想要实现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是关于孩子们的存在。我们看到那位单身母亲早织,她全身心地抚养自己的孩子。她有时可能显得有点专横了,但她是位好母亲。我们在日语中有个特殊表达,指的是当你扣一件衬衫的纽扣时,把最上面一颗纽扣扣错了——这是个小错误,但会让你把整件衬衫的纽扣都扣错。一个小错,或错误的判定,可能导致一切失控。大概就像这样。然后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老师身上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是他有什么显著的缺点——其实一点也不。可一旦他迈出错误的一步,事情就会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生活不会因你而停止。最终,两人都意识到孩子们所处的情境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也许家长会认为这是件令人绝望和担心的事情,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把它看作一种可能性。孩子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无法到达——我认为这是希望之源。我在片场工作时,这种想法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当然能在结局中看到希望的元素,但我比较想听你多讲讲你认为这种影片结构性动态中有什么包含着希望。
好吧,我不想剧透任何内容……在我眼中,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些孩子想让世界终结,这样他们就可以重生的。
但是,这种重生意愿最终开始奔向一个不同的未来。那样看的话,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你之前说你在结尾感受到了希望,我的确希望那是你的观影感受。换句话说,我乐意相信小主人公能够在情感上支持肯定自己。我希望他能够到达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对自己说:一切都好。
这是自《小偷家族》之后你在日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之前你在法国拍过《真相》(La vérité),在韩国拍过《掮客》。你认为在国外拍摄这些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你作为电影人的身份吗?之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日本演员和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再次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拍片,又是什么感觉?
唔,它有改变我吗?我觉得在法国和韩国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帮助了我成长。在那些情形下工作就是在学习如何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把内容刻画出来。那很吸引人,但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而回到日本拍摄(《怪物》)这部电影,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比清晰。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这部分工作是确信无疑的。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之前参与过外国电影项目的拍摄,还是因为这次我可以自由执导别人写的剧本,但即使是和我之前在日本拍摄的所有经历相比,这次的一切也变得更清晰了。拍摄时我有种强烈的信念。但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因为什么。
《怪物》里有很多是枝裕和式的母题和主题,一想到这个本子竟然不是你而是别人写的就会觉得很惊讶。我脑海中浮现的你常拍的主题之一就是制度的不可靠性。在影片的成年人角色中,最终似乎是校长最接近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的境地。但当这场危机爆发时,她和学校在为学生和老师服务方面都做得非常糟糕。这里体现出了一种制度对风险的反射式规避,以及一种对探寻和理解情境具体细节的无能为力或不作为。这让我想起了《小偷家族》的结局,电影中的角色们所面对的社会制度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人一起经历了什么,也无法理解他们需要什么。你认为你的这种电影制作倾向是一种社会批判吗,尤其是在日本的社会背景下,还是你认为这只是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悲剧的可能开展方式?
唔,说到坂元裕二的剧本和我的作品之间的重叠主题,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俩尽管属于不同领域,但总是在探索类似的问题——忽视了亲情的原生家庭与后天找到或选择的非原生家庭。
主题上,我们一开始就互相关联,而我想这就是他们找我来执导的原因。但你这么说在我看来并不意外,因为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说这是我作品的一次自然延伸。甚至有几次在我们拍摄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个剧本不是我自己写的。
至于你所说的关于社会制度的评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日本,我们会看到牺牲个人来保护组织或制度的例子。我确实认为学校在这个故事中是一个典型例子。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片中那位老师的个人爱好——在报纸和出版物上寻找拼写错误,然后把它们邮寄给出版商。他的女友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更好的爱好?”而大多数人,可能包括出版商本身和整个社会,都不会觉得他的这种习惯会有多大用处。但最终,正是这一点让他意识到事情是怎么回事,并最终拯救了他。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反转——集中注意力并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独立个体,最终能获得对事物极有意义的认知。
《怪物》似乎非常流畅地横跨了两种电影类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展开方式几乎像一部悬疑惊悚片,然后第三幕过渡到另一种叙事基调和模式,更接近你那种精妙的剧情片类型。而直到看完这部电影,我才完全欣赏到你是如何毫不费力地完成这种类型跨越的。
在我接下这个项目时,这正是让我最感兴趣也最担心的事情之一。影片的前三分之二有推理和悬念的元素,我以前从没在电影中探索这些元素到这种程度。在头三十分钟左右,当我们跟随着这位母亲的时候,我们需要感受到她的经历是多么令人不安——有些事正在发生,但我们并不完全知道是什么事。我之前就明白这部分必须吸引住观众,并把他们拉入故事中,这与我以前拍过的很多电影非常不同,那些电影更多展示的是生活片段。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所以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我希望我们也能谈谈坂本龙一。我不知道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但,我对你失去同事以及可能的朋友表示哀悼。
我们不算是密友。他是我一直远远保持敬仰的人——他的话语,他的创造力。我一直很尊敬他,就像尊敬一位年长的艺术家长兄一样。他当时就身体不太好了,你知道的。他当时说话有困难,所以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我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他看了这部电影,非常喜欢。他说他很难完成全部的配乐。他说:“这部电影在我脑海中勾勒出了一些画面,让我试试看吧。”最后他为这部电影完成了两首新曲,我另外用了他去年12月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12》中的两首音乐。在剪辑过程中,我用了他早期的三首曲作为临时配乐,最终我也得到了在电影中使用这几首曲子的许可。当然,对于他的离世我很难过,但我很骄傲能与他共事。
对我来说,整部电影中最感人的场景之一就是以音乐为中心的小段落。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在所有三幕中都体验到了这种感觉。一开始,配乐并不明显,听起来只像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在练习一些号角类乐器。但在最后一幕中,我们发现其实这是主人公在第一次试图吹奏长号,而且它带来了某种特定信息。校长告诉他,要带上他所有的伤痛和困惑,然后用乐器把这些情绪都吹走——本质上,就是用情绪来创作音乐。你把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放在电影中的方式——以一种最初如此引人注目(译者注:怀疑原文有误)但却意味深长的方式——让人感觉非常像坂本。这也是一种对音乐之力的相当美好的阐释。如果把这解释为对他的某种致敬,会不会有些夸张?
这个场景在他参与这部电影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坂本龙一拒绝了我对他参与这部电影制作的邀请,我会在没有任何音乐和配乐的情况下拍摄这部电影。这就是我如果用就一定要用他的音乐来制作这部电影的决心。但我对那个场景也有同样的感觉——即它是如何与坂本及其音乐同步的。当我把剪辑版本发给他时,他在反馈中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有多喜欢音乐教室里的那个场景。他为此称赞了我,并说:“我写的配乐不会干扰我们在那个场景中听到的音乐的共鸣。”他说他觉得我们不该在这个段落加入任何额外的配乐。我想那个小场景带出来的情绪和信息给了他非常强烈的感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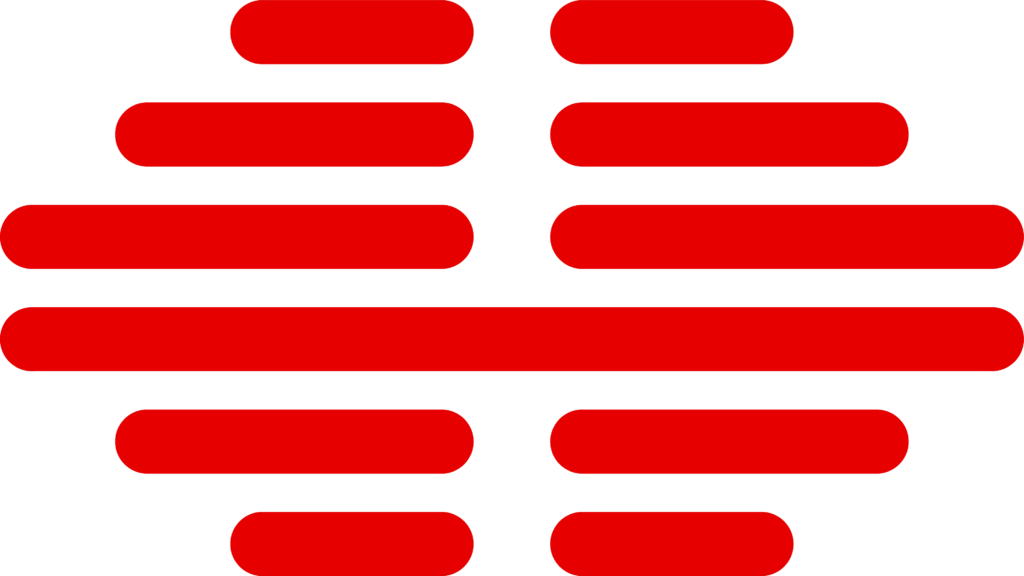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Patrick Brzeski | The Hollywood Reporter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