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娜·科布(Anna Cobb)参演恐怖片《我们都要去世界博览会》(We’re All Going to the World’s Fair)
用户生成内容(UGC)既是电影的未来,也是现状。当我们以不那么感性的视角回顾2022年的电影,我们会看到TikTok浪潮、Instagram Reels短视频、Twitch流媒体平台、YouTube上的各种反应视频和OnlyFans的色情片。在电影消亡之前,你可以看到Ring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以“美国最滑稽的警察”风格重新包装,制作成在多个平台上播放的家庭喜剧《Ring Nation》在2022年首播(由同属亚马逊的安全摄像头品牌Ring和米高梅电视共同出品)。
由具有高分辨率、更大的存储容量以及无处不在的消费级数字摄影机所录制的数字图像数量激增,这是本世纪才发生的事情。这些图像是大银幕和小荧屏之间争夺观众眼球的武器——随着家庭观看取代了影院观影,这些图像就成了流媒体过剩的现成档案素材,它们是犯罪纪实电影、小报修正主义和快速周转的搜索引擎优化回填的系列纪录片的填充,这些影片通常是由那些不再费心看完自己拍摄的素材的知名电影人执导。
但是,说真的,当我刚刚提到大银幕和小荧屏争夺观众眼球时,我更多描述的不是你选择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在家观看任何内容,而是你的眼神在客厅的电视机荧屏和手中的电话之间来回移动。
现实生活中的“记录”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之频繁,以至于让人头晕目眩,所以我认为今年大多数真正成功的电影都是由那些看起来真的有好好研习过自己的家庭电影和个人记录素材的电影人制成的,这并不是一个巧合。他们的探寻正是花时间来坚定地体现出,当我们一直在创造图像时,我们就是一直在创造意义,创造艺术。
在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自传小说中,她经常使用描述自己的一张旧照这种方法,客观地叙述照片的外观,照片和过往当中蕴藏着主观性,她会以不说“我”的方式去除这些东西表面的主观性,让这些描述既关于她,又不是她。在某种程度上,她在影片《超8岁月》(Les années Super-8,该片由她和她的儿子大卫·埃诺-布里奥-David Ernaux-Briot共同执导)中重复使用了这个技巧。影片追忆了1972年到1981年拍摄的几卷家庭旧照。家庭迁移,孩子长大,世事变迁。正如埃尔诺的书中所述,她曾经的“我”是她自己的一个版本,与法国的乡村历史、贫困、左翼政治理想主义有更多的联结。在《超8岁月》中,这种理想主义被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所淹没:圣诞节的玩具、家居陈设、滑雪装备,这些物品全部都以摄影机的饱和色调呈现,本质上是终极成就和放纵,其捕捉到的每一帧图像都是对不断累积、被包裹住的消费者舒适的含蓄颂扬。
埃尔诺是战后巴黎郊区生活最优秀的观察者之一,她所观察的法兰西岛大区快铁B线沿线生活,也是爱丽丝·迪欧普(Alice Diop)的纪录片《我们》(Nous)的主题。该片包含法国-塞内加尔的迪奥普家族在世纪之交拍摄的家庭视频,带有熟悉的像素化图像质量和明显的摄影机时间戳,展示了在“我们”这个集体名词边缘的移民社区的生活。在迪奥普的电影《圣奥梅尔》(Saint Omer)中,同为作家的角色拉玛(由凯伊洁·卡戈梅-Kayije Kagame饰演)在一所大学的课室中上课,这所学校的课室远比埃尔诺曾任教的任何地方都更好;然而她的“我”依然难以捉摸,就像埃尔诺的“我”一样——她的“我”也许是一个他者。
当拉玛出席一名法国裔塞内加尔母亲溺死自己孩子的庭审时(正如迪奥普出席那场轰动性的庭审,这是《圣奥梅尔》的故事原型),法庭上的证据让她在主观上对被告产生了一部分共情,这些证据让她感到不知所措。迪奥普用真实的庭审笔录,从法证角度审视档案,发现了一位精神上充满野心的移民的双重意识和母女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拉玛的回忆里,这段回忆使用的录像机素材是了为这部片而专门表演的段落,而这些素材看起来与《我们》的真实家庭电影有种诡异的相似。
“我不想失去有关任何人的真实记忆。”南·戈尔丁(Nan Goldin)在《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中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这部作品是献给她的姐姐芭芭拉的,她在南11岁时自杀。《性依赖的叙事曲》中的照片以破碎的魅力、朋克式的同理心、浪漫的堕落、药物滥用、早夭和永恒的姿态形成了一本重组家庭影集。这是对出现在劳拉·珀特拉斯(Laura Poitras)的纪录片《所有的美丽与血泪》(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中自己原生家庭影集的一种法斯宾德式的即兴重复的回应,也是一种讽刺的对照。这部纪录片中包含年轻的芭芭拉在战后囿于家庭生活的珍贵照片。这种压抑的家庭生活将芭芭拉的个人特色活活扼杀。(另一幅宝贵的照片终于不再被压抑:在塞巴斯蒂安·利夫施兹-Sébastien Lifshitz的纪录片《苏珊娜之家》-Casa Susanna中,在卡茨斯基山脚下的一个同名的异装者聚集地中拍摄的照片几十年来首次带来了曙光,但这道曙光来得太迟,无法摧毁或拯救任何人的性命;拍摄对象身着百货商店的皮草、高跟鞋和高发髻,这些都象征着他们真实且隐秘的生活,散发着讽刺的魅力,彰显着他们自身风格张扬、表达压抑的西尔克式语言。)
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曾自制自己的学生电影,并将其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纪念品》(The Souvenir),影片分为第一和第二部分。2022年她带来了电影《永恒的女儿》(The Eternal Daughter)。这是一部关于一位电影人尝试与过去的鬼魂进行交流的惊悚恐怖片,鬼魂“朱莉”(由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饰演)即她熟悉的电影人人格。通过将她母亲带到她熟知的地方,希望能在还来得及时坦白故事,揭示启发。而在夏洛特·威尔斯(Charlotte Wells)的《晒后假日》(Aftersun)中,正如《圣奥梅尔》一样,父母与孩子的亲子联谊之旅采用了世纪之交时期的录像机素材;这信号有瑕疵且欠饱和的图像大概是银幕中的女儿拍摄的,在这样的图像里,以威尔斯已故父亲为灵感而创作出的角色——片中的单身父亲卢姆,通过过时的影像格式中的视觉碎片,通过这样的人造产物呈现出来,打造出一个既近的触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的过去,就像过去很久的假期和《超8岁月》中一闪而过的前夫的画面。
电影的鬼魂不胜枚举:安妮·埃尔诺的前任,南·戈尔丁的姐姐(以及其他人),乔安娜·霍格的母亲,夏洛特·威尔斯的父亲,爱丽丝·迪奥普的父母。在通灵板附近还留有一个男孩的位置:小萨姆·法贝尔曼,他在自己的家庭电影中找到了自己,也在其中丢失了父母的影像。《造梦之家》(The Fabelmans)中,有一个精彩的法贝尔曼一家露营旅行剪辑桌的段落,萨姆在期间发现自己母亲的情感不忠。这部电影将美国大片制作的整个机制的原始场景定位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自己的超8岁月里。我们知道,美国主流电影叙事的情感核心是——令人肾上腺素狂飙的兴奋感、新奇感、恐怖感和安心感。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围绕银幕上核心家庭的分离与团聚的情感操控都被视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感内核可以追溯到婴儿潮一代,在此期间出生的孩子,和埃尔诺一样,因为自己的家庭真正开始变得富裕,当时得到了一个新玩具,而如今,这批人痴迷于2022年所拍摄的关于2022年银幕上家庭假日的另一份私人摄影档案,他们尝试找到事情开始出错的那个瞬间。
下一个萨姆·法贝尔曼在一个陌生的UGC新世界中在线上寻找/迷失/创造了自己。在简·申布伦(Jane Schoenbrun)的这部《我们都要去世界博览会》中,在语境坍塌的世界里发生了一场屏幕共享的历险。青年凯西(由安娜·科布饰演)在暗网的无尽深渊里探索,里面有各种表情包、恐怖故事和(也不知是出自谁的)拾得录像。她一脸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表情像极了你常看到的Z世代在手机上茫然地敲着键盘,结果发现他们是在发类似“莪真啲要尖ロㄐ了omg”之类的推特。尤其是考虑到《造梦之家》在首映过后,比《我们都要去世界博览会》更快上线流媒体,凯西的那位更年长的在线对话者/导师/狩猎者,这位并不确定该把凯西当回事还是讽刺地看待她的网友,可能代表的正是斯皮尔伯这套极度真诚的胶片电影、院线上映、鸿篇巨制(的受众),对于《我们都要去世界博览会》中令人不安且的我策划的数字糟粕推文和令人费解的打字方式,他们会困惑地敬而远之。
(虽然如此,但请允许我再提一部越来越少见的正在崩塌的杂揉多种类型的电影:在《不》-Nope中,“新斯皮尔伯格”乔丹·皮尔-Jordan Peele导演让他的角色们,大部分为非白人角色,讲述了自己亲历名不副实的恶名的经历,还保留了影像资料——有的是老西部电影式的,有的是情景喜剧式的。片中用到一台虚构的结合了个人化与通用化电影制作技巧的手摇式IMAX摄影机才让这个自图像能动起来以来就“投身电影界”的家庭最终拍出了自己的家庭电影。)
在2022年,我们还见证了数字世纪标志性的艺术作品之一的延续:电影《蠢蛋搞怪到永远》(Jackass Forever)延续了《蠢蛋搞怪秀》剧集和电影系列的传统。该电影系列采用数字摄影机来捕捉一群老友的滑稽表演。随着年纪的增长,演员们看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早期带有颗粒感的录像机时期的感觉,就像爱丽丝·迪奥普和夏洛特·威尔斯的家庭电影,都展现出饱经风霜的家庭相册中的辛酸过往。《蠢蛋搞怪秀》诞生于高端消费级数字摄像机的早期阶段,但其根源和灵感可以追溯到YouTube出现前,那些年最火的是一些业余的滑板视频。YouTube和那十年出现的所有主流视频平台一样,都是从最早的用户上传的《蠢蛋搞怪秀》模仿片段发展起来的。那十年里,好莱坞也从胶片制作转向数字制作。本质上,《蠢蛋搞怪秀》系列中捕捉到的濒死体验之一就像电影本身濒临死亡。
和《蠢蛋搞怪到永远》一样,《未来罪行》(Crimes of the Future)讲述了一位银发的行为艺术家索尔·滕泽(由维果·莫滕森-Viggo Mortensen饰演) 拍摄自己的自残行为的故事。他有着和《蠢蛋搞怪秀》里的约翰尼·诺克斯维尔(Johnny Knoxville)一样的银灰色头发,和饱经风霜的面容(甚至他的表演也明显受到了片场之外很像诺克斯维尔会受的那种伤的影响:他被一匹脱缰的马撞到)。和《蠢蛋搞怪秀》的没落一样,索尔接受了自己身体的消亡和衰退,他拍下了自己身体内部像肿瘤一样生长的“新器官”——这是终极的UGC形式。
索尔患有“加速进化综合征”,但导演柯南伯格所青睐的富有见地且中立的台词总是带有一些后人类主义的意味。《未来罪行》的结尾,在索尔的身体将合成材料转化为营养物质时,他的表情抽搐中却又带着激情,我选择相信未来仍有希望。他的表情是痛苦但充满喜悦的。电影画面是数字化的,是看起来有点脏兮兮的、带有污点的黑白画面。整个过程都是由索尔的同伴用低分辨率的鱼眼镜头搭配小到可以装在一个戒指上的个人摄像机拍摄。电影尚未死亡,只是正在经历一场形态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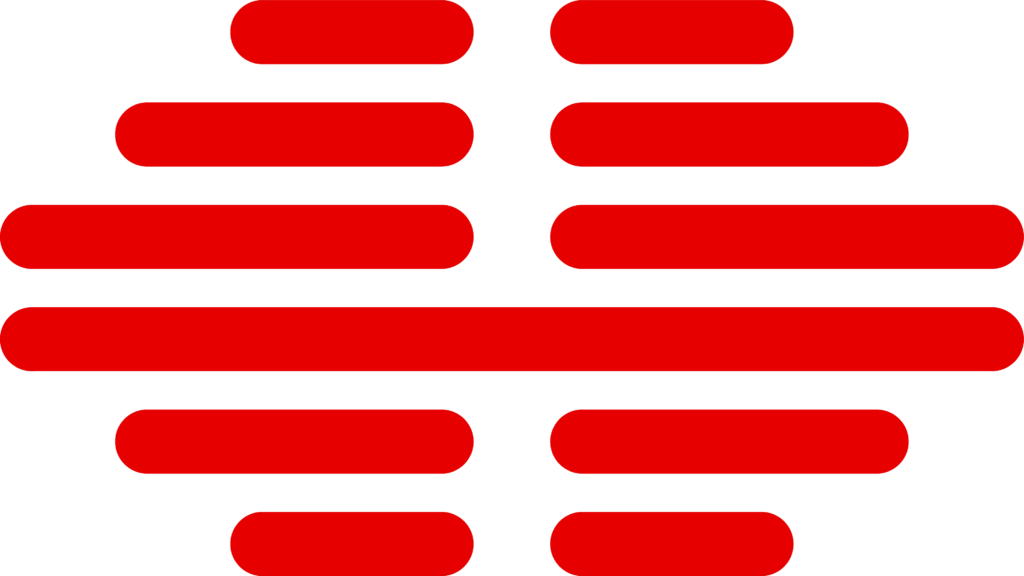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Mark Asch | Filmmaker Magazine
翻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