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杀手》中饰演杀手的迈克尔·法斯宾德
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的《杀手》(The Killer)是一部精简到只剩下最基本要素的电影,与片中描绘的杀手主人公有着一致的风格。这部改编自法国连环画的电影由安德鲁·凯文·沃克(Andrew Kevin Walker-《七宗罪》-Se7en)改编,讲述了一个无名的杀手(迈克尔·法斯宾德-Michael Fassbender)和他恪守严格行事规则的故事。这个杀手只在乎工作过程中的行事规则,并不关注道德困境,但当他搞砸了一个暗杀任务后,这些不同方面令人难以忍受地互相纠缠在了一起,并且后果影响到了他爱的人。
表面上看,《杀手》是个复仇故事。杀手的暗杀任务严重出错,而其伴侣玛格达拉(索菲·夏洛特-Sophie Charlotte饰)遭受了暴力袭击,此时法斯宾德饰演的无名杀手便打破了自己的规则,追查那些要负相关责任的人。《杀手》是个充满阴影,反社会者和他们刺杀对象的世界。对于法斯宾德饰演的反英雄人物来说,感觉自己反过来成了猎物是个非常新奇的概念,而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重新校正这个世界,以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合格的“捕食者”。
这是导演芬奇与摄影指导(DP)埃里克·梅塞施密特(Erik Messerschmidt)的又一次合作。后者此前与芬奇合作担任了《心灵猎人》(Mindhunter)和《曼克》(Mank)的DP。在《杀手》中,梅塞施密特协助芬奇将观众置于主人公难辨而冰冷的视角中,优雅地掩藏了他所制造的混乱。本文中,我们和梅塞施密特谈到了他和芬奇的工作关系,以及将《杀手》带上大银幕是什么感觉。
《杀手》对其反英雄主人公那套职业行事规则的详细描述令人意外。将主人公的世界搬到大银幕上是种什么感觉?
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冗余和单调感的。我认为大卫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拍摄出这种感觉。我不会说我对此感到不舒服,但我很紧张,觉得观众可能不会完全投入到这种拍法里去。我们谈过这个。我说:“天啊,有这么多篇幅都是他坐在车里观察别人。我们要继续这么拍吗?”大卫则说:“我们要试一试。”我们合作过这么多次,彼此间已有一套非常清晰直接、心照不宣的沟通方式了,而且这次我们能够非常直接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并不总能这样。

图源:Netflix ©2023
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关键之一就是过程和展现,几乎像是电影制作本身。
是的。说实话,我觉得这非常巧合。杀手和电影导演之间有相似之处吗?我想是有一种类似的过程。
这部电影也是关于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以及我们如何讲这些故事的,是不是?
当然是。我认为我们一生中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欺骗自己。我们对自己在信心上撒谎。我认为这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关于自信导致的悲剧,以及其中包含的脆弱性。我觉得这个杀手主人公真的很想相信他能完全控制住一切。当然,当他走到最后,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让他通过这一整个过程,找到了一点醍醐灌顶的感觉。这几乎像是那种不存在绝对控制权的拔高版的现实。如果你想的话,你当然可以批判它或者从哲学的角度探索它。

图源:Netflix ©2023
或者你也可以欣赏简洁利落的风格元素,比如杀手和佛罗里达州某个男人之间残酷的打斗场面。它是如此的黑暗和生动。你是怎么拍出来的?
我此前从未像在这部影片中那样清楚意识到声音在电影中的作用。而你瞧,电影制作是个非常专注自身领域的行业。如果你是个DP,你通常会非常关注图像,关注摄影。而在我们拍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些东西,比如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观众理解角色在房子什么位置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观众在穿过房子的时候能在头脑中建立一个虚拟的3D环境模型。我们对屏幕的朝向非常一板一眼,并且我们非常关心剪辑。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用长焦镜头拍摄,看镜头里的东西翻来滚去。我们希望你能从这个场景中得到更多背景信息。不过还有一点,我们当时非常积极地讨论过,影片中的什么信息观众可以靠推断,什么信息观众可以通过声音理解,以及什么是观众需要看到的。
那场戏是怎么准备的?
那场戏我们准备得不能更周全了。我们的特技指导戴夫·麦孔布(Dave Macomber)编排了这场打斗。他们用纸板箱模拟了房子。他找了个特技团队试拍了一遍这场戏。我们在考虑屏幕朝向的同时做了关于镜头覆盖的笔记。然后他回去,再试拍了一次。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不断打磨完善,再打磨完善。然后我们才开始考虑:“OK,我们希望这里有光。这里不能有光。确保一切都保持一致的实际情况如何?”我给整栋房子都布了光,然后我们有条不紊地穿过它拍了这场戏。
就像你说的,你从未像在这部电影里那样思考过声音的运用,那么采用史密斯(The Smiths)乐队的音乐对你的拍摄选择有多大影响呢?
是的,那是后来加的。芬奇当时在放史密斯乐队,而他知道他想在片中用上《How Soon is Now?》这首歌。他们讨论了在声音变得主观的段落之间的剪辑方式。你会听到角色耳机里的声音,然后你会在摄影机不拍他心理活动时听到耳机里微弱溢出的声音。我们讨论过这些,但原声带和史密斯的部分我觉得大卫是在剪辑阶段才决定这么做的。
就大卫·芬奇的电影来说,作为观众,你总会觉得自己被照顾得很好。从一开始,你们是如何定下基调并请观众代入杀手视角的?
我觉得我们说的是:注意看这里,这里很重要,然后我们就直奔主题。这很重要。有点像是故意投喂观众看这些。我们想带你经历一段旅程,给你一次体验。这包含了画面里的所有东西。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次剪切,都是经过讨论和考虑的。我们做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事无巨细,比《心灵猎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卫对我们如何在画面中包含各种元素,以及迈克尔该在构图中什么位置的安排,比我拍过的任何一部电影都要精确。

图源:Netflix ©2023
在创造这些体验的过程中,RED摄影机带给你们的体验如何?
我们已用RED拍了好多年了。事实上,大卫用RED拍电影的时间比我长。他是从《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开始用RED摄影机的。我本质上并不认为摄影机会对图像有任何实际的影响,我认为这种想法对电影来说是种罪过。觉得摄影机选择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审美风格是不对的。我觉得这简直是对摄影技术的侮辱。摄影机有一定的特性和一定的功能,会影响你可以拍摄的类型,但我也希望用Alexa一样可以拍到某种程度上类似的图像。
摄影机就只是工具,对吧?
就只是工具。就像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弹Stratocaster吉他是因为埃里克·克莱普顿喜欢这种吉他,但他也可以拿一把Les Paul吉他演奏,只是他选择弹Stratocaster罢了。我不觉得克莱普顿会认为这是把更优秀的吉他。它只是他用着最趁手的工具罢了。我对摄影机也是同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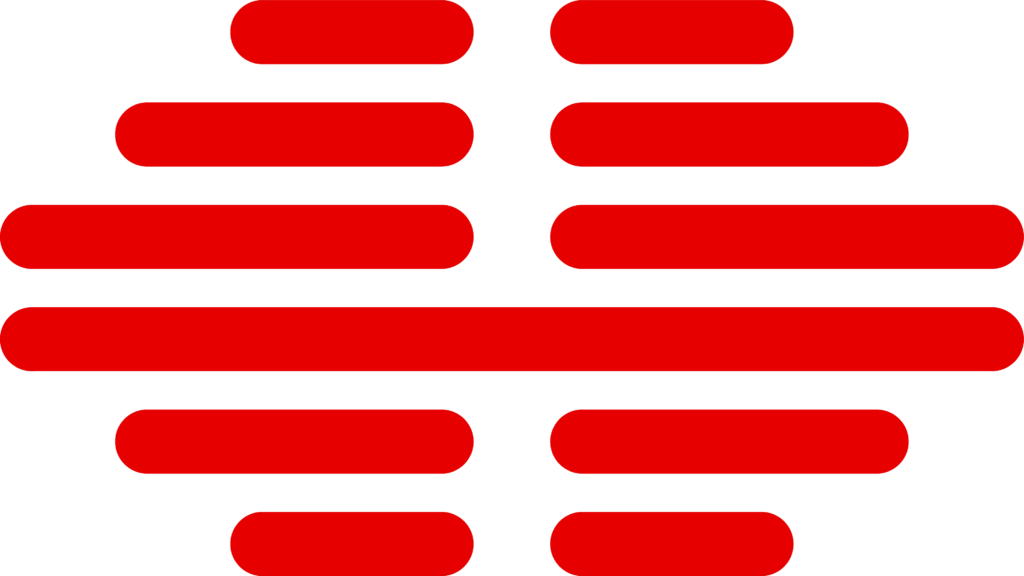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Jack Giroux | The Credits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