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剧席琳·宋(Celine Song)出生在韩国。在她的导演首作《过往人生》(Past Lives)中,她制作了一部浪漫且看似简单的电影。影片故事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自传性,但同时又具有普遍性,其主题是爱情、失去和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过往人生》分成三个部分,横跨多个国家和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首先,我们会看到一个名叫诺拉的韩国女孩,小时候她与一个名叫海成的男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随后她与她的家人一起移民到了多伦多。然后我们会看到20出头的诺拉与海成在网上重新建立了联系。十多年后,海成拜访诺拉,现在她已经是一名住在纽约的已婚编剧。影片由格蕾塔·李(Greta Lee)、刘台午和约翰·马加罗(John Magaro)主演。
我和宋谈了《过往人生》的后期工作流,以及制作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的A24电影的经历。该部影片还获得了电影独立精神奖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奖项。

ℚ 你是如何为你执导的首部电影做前期准备的?你是否有和其他导演进行交流?
我和一些出色的导演进行过对话,但他们都说,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制作的电影,所以准备的过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需要非常给力的制片人和各部门负责人,我很幸运这些我都有了。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我都能够借鉴他们的经验建议。
ℚ 你是在首尔和纽约取的景。回到首尔对你来说是故地重游,还是说是种与众不同的经历?
这两个地方的电影制作文化有很大差异。在纽约有很强大的行业工会,但韩国没有。并且,在这两个地方,预定取景地的方式也有有所不同。在纽约,如果你想在什么地方拍摄,那么市长办公室一定要对此知晓。而韩国则有点像游击式拍电影。你只用去到那个取景地,尝试在这个地方取景。在韩国你不太能获得许可。
ℚ 影片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间范围内。你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拍摄的吗?
不。我们在纽约拍摄了所有素材,然后为Skype的剧情搭建了一套布景。随后我们去到韩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在韩国再拍摄了10天。
ℚ 你和你的摄影指导(DP)沙比尔·科尔奇纳(Shabier Kirchner)用35mm胶片拍摄来这部电影。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个决定?
这是我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所以我并不清楚制作的难度会有多大。我之前没有数字拍摄和胶片拍摄的经验。我什么都不了解。我觉得这个选择的一部分原因是新手的勇气吧。无知者无畏。无畏精神就是这样来的。但这个选择也是从我和我的DP进行的对话中产生的。我们讨论了影片的故事,以及胶片拍摄的理念如何与这部电影的理念——时间成为有形,时间变得可见——产生联结的。因此用胶片来拍摄这部影片就成了合理选择。

ℚ 你是出身于戏剧背景的,很明显戏剧没有任何的后期制作可谈。这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很陡峭的学习曲线?
是的,但在戏剧中会有一个预演期(preview period),你会看到你的戏剧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且你能以这种方式继续进行编排修改。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一名编剧。所以对我来说,后期制作的一部分是,我不认为这部电影仅仅是我在银幕上看到的,以及所有的声音设计和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对我来说,电影就像一份文本。就像我会修改我剧本的每一部分一样,我感觉我看待电影后期流程的方式和修改剧本是一样的。
当然,在电影中,不仅仅是在纸上编写剧本。还有声音、色彩、视觉图像、时机……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我真的感觉后期制作就像在谱写一首曲子。我将电影看作是一首乐曲,它有它自己需要保持的节奏和韵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和我作为剧作家要做的部分工作一样,就是要创造一个从头到尾都像一首乐曲的世界。
将这一点时刻铭记于心后,我真的感觉我为进行后期制作进行了最充足的准备。我有一整个世界可以去学习;之前我从没这样做过。但对于后期制作,我如鱼得水。我非常喜欢影片的剪辑与视效的另一个原因是你可以拥有许多掌控权。比如说在剧场中心位置有一根杆子。在戏剧中,你只能接受这根杆子的存在。但在电影中,你可以用视效直接移除它。非常神奇。
ℚ 《过往人生》的剪辑师基思·弗雷泽(Keith Fraase)住在纽约,他是亲自来到了韩国取景地现场,还是你将样片发给他?
我们发送样片给他。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他无法来到现场。
ℚ 这部影片遇到的最大剪辑挑战是什么?

我认为这部影片与我最初编写的剧本没有太大差异,所以更大的剪辑选择已经写在剧本上了。更困难的部分是那些基础的内容——将整部电影衔接起来、但却不是情感核心或故事核心的场景。
比如诺拉去到蒙托克的场景,我们知道她最终将见到亚瑟(她未来的丈夫)。我们要解决的是,双方遇见需要多少时间,如何表达时间,这样当我们见到亚瑟时,感觉就像二人自然而然遇到,并非刻意安排。我编写了所有我们拍摄的这些非常基础的内容——她前往蒙托克的旅途中的每一个故事节奏。我们有地铁的节奏;我们有巴士的节奏。我们拍摄了许多她前往蒙托克的素材片段,因为我对这部分剧情很紧张,感觉不够长。当然,后来当我们开始剪辑时,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的只有几个素材。你会意识到,场景的节奏再一次决定了你并不需要用上所有的素材。
ℚ 你们是在哪里进行所有的混音工作?
我们在纽约的Goldcrest进行所有的混音工作。
ℚ 你是否深入参与到了混音工作中?
非常深入参与,你完全无法想象。我认为混音是唯一一部分需要我花更多时间的工作。我们超了预算……这只是更委婉的表达方式。这是后期制作中唯一一个我提出很多要求的环节。我对这一环节非常着迷。影片的声音设计师给我取的外号是“废寝忘食女士”。我知道不同的导演对于混音工作有不同的工作流程,但对我来说,我在混音室和声音设计师雅各布·鲁比科夫(Jacob Ribicoff)每天工作14小时,一周工作五天,有时还会加班长达几周。我不会离开。
我待在那是因为我知道声音是将整部电影衔接起来的元素之一。并且,在这部电影中,各个城市的声音设计,它们之间的迥异差别,以及声音和构图如何配合——对于我想让这些元素如何改变,我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因为,这是我第二次说这句话——我将电影看作是一首乐曲。所以我对它十分疯狂。但我不想让人们注意到影片的声音设计。我想让人们能感受到,他们仿佛就站在麦迪逊广场上。我想让他们完全沉浸到影片中。
ℚ 显然,这部电影并不是那种视效密集型的,但还是有一部分视效的。这些视效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我认为视效是一个有点主观的东西。实际上,当我看到视效时,我想的是:你觉得这看起来效果好吗?我将它展示给我的美术指导和摄影指导(DP),并对他们说:我觉得这看起来不错,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做得更好点。你能看看吗?我需要参考许多人的意见。

我很相信基思,也很相信我的剪辑助理香侬·菲茨帕特里克(Shannon Fitzpatrick),她是捕捉视效问题的高手,对细节有着敏锐的察觉力。我认为她是少数几个能在视效中发现我发现不了的问题的人之一。当我觉得某个视效看起来不错时,她会指出角落里的一个还不太行的地方。在A24中,也有很多擅长捕捉声音和视觉图像问题的人才,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会指出听起来不太对劲、或者看起来有些奇怪的地方。这样一来,你就有了许多人成为了制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ℚ 这部影片的调色师是谁?你在调色的参与程度有多少?
是来自Company 3的汤姆·普尔(Tom Poole)。我们在Company 3进行剪辑、调色等所有后期工作。我很喜欢调色的过程,因为我在沙比尔之后才加入调色流程,此时汤姆已经将整部电影过了一次,并完成了调色。他们调出的作品非常优秀,画面精美。随后我加入,对特定场景给出注释,随后我们一起调色。当然,当他们在做调色时会给我发送静帧,而我会在去调色室前对静帧做出注释。并且,沙比尔和汤姆也经常合作,所以他们对于想如何给影片做调色已经有了默契。
ℚ 你打算制作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由于这是我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我觉得我的主要目标是要发现我自己电影的语言。从剧本编写阶段到后期制作,这不仅是试图以我所能的最佳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认为这是整部电影的目标。但事实是,我真的希望电影的语言成为我自己的语言,我想学习并认识到我自己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ℚ 我知道这部电影的其中一部分也是你的自传。诺拉身上有多少是你自己的影射?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个真实发生的事——我的青梅竹马从韩国来看我,我和我的丈夫住在纽约,我坐在他们二人中间。所以这部电影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自传,我在那一刻的感受是整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但一旦你将这件事写成剧本这样一个客观化的过程,然后拍成一部有数百人参与的电影——尤其有是那些需要扮演角色的演员——那时它就成了一个客观事物。至于后期,这是一个精雕细琢的过程。重点在于把一个将与全世界分享的事物组合起来。

ℚ 电影与编写戏剧有很大不同。这对你来说是否是个很大的调整?
我了解戏剧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一行工作了十年时间,可能更长,所以我很清楚戏剧的制作方式和电影制作方式的本质区别。例如,在戏剧中我学到,时间和空间是象征性的,而在电影中的时空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在讲述一件横跨两个大洲和数十年时空的事件上,两种媒介各有优劣。而且在这部影片中,因为荒唐的是,故事中的反派是长达24年的时间和太平洋,这实际上需要时空切实可见地表现出来……因为两个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需要有一个原因。所以,那对少年少女必须真实存在,而韩国和纽约需要让人感觉是实际存在且真实的。
ℚ 我想你应该对执导下一部作品感到迫不及待了吧?
噢我已经等不及了。我想明天一睁眼就去到片场。我是这样想的。我正尝试尽快拍摄下一部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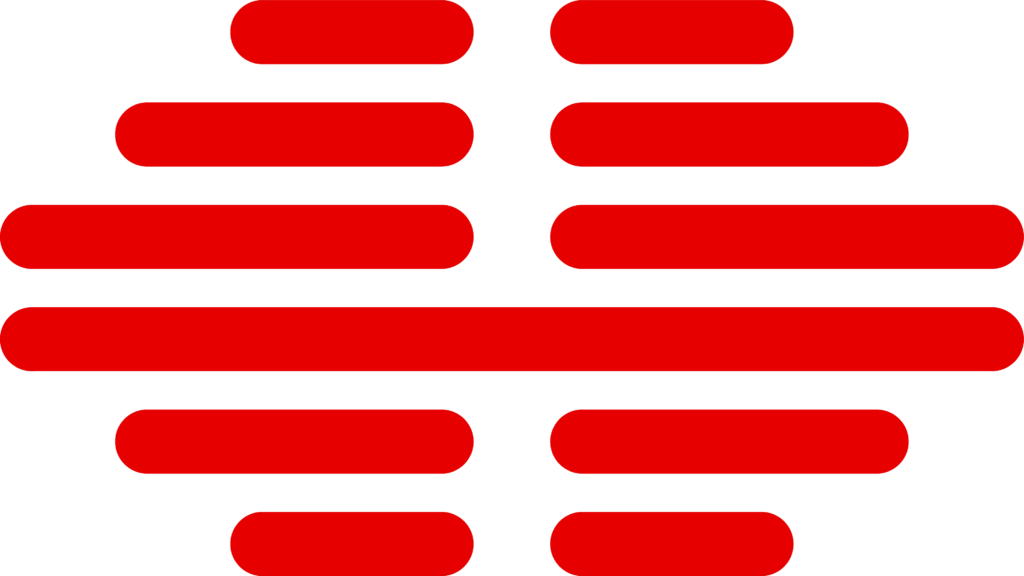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Ian Blair | postPerspective
翻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