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剪辑师凯文·坦特(Kevin Tent,ACE)与导演亚历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合作多年,二人合作制作的作品不胜枚举。他们第一次合作的电影是1995年的《公民露丝》(Citizen Ruth),自那以后佩恩所有的电影都由凯文剪辑,包括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杯酒人生》(Sideways)。坦特凭借他在《后裔》(The Descendants)中的出色剪辑首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认可。
这一次,凭借为佩恩的新作《留校联盟》(The Holdovers)担任剪辑师,坦特再次受到奥斯卡提名。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忧参半的假日电影,讲述1970年冬假期间,聚在新英格兰的一所寄宿学校的三个孤独的人。我与坦特讨论他的工作流和为这部斩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做剪辑的经历。

图源:Peter Zakhary
你是如何开启这次与亚历山大的合作过程的?
当他有了初步构想时,他和编剧戴维·赫明森(David Hemingson)甚至还没写出完整的剧本。我读了前几版剧本,即使还很早时它就已经呈现出很好的状态。我会给他提供我对剧本的意见等等,而他会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意见。随后,当他们开拍时,我马上就开始剪辑。
亚历山大告诉我,在他执导的早期电影中,比如《公民露丝》,你会去到片场,但从那以后就没有怎么去了。
是的,和往常一样。我待在洛杉矶剪辑这部电影,而他在波士顿拍摄。我确实很喜欢去到片场,哪怕只是待一天也好,跟在场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打个招呼,但当你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二十分钟后,你会想:我来这究竟是来干什么的?所以,我就没有花太多时间待在片场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剪辑室里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因为他一边拍摄,我一边顺片。
我猜,在拍摄时你们应该会持续保持联系。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至少沟通一次。如果他想看的话,我通常会在周末给他发送剪好的场景,但在最近的几部电影合作中,他在周末休息时不太想看剪好的场景。我觉得是他有太多其他拍摄问题需要处理了,没有时间看这个。
他也不看样片了,但我们的合作依然顺畅,因为当他回到剪辑室时,他能以全新的眼光观看样片。并且到那时我也相当熟悉这些素材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并且剪辑过。所以,当我们一起开始剪辑时,我们都处于相同的状态下。

我知道亚历山大拍摄是非常精确的,这是否意味着你无需观看和剪辑一大批素材?
是的,他对这部电影的镜头覆盖非常精确,这点很好。他对他的镜头覆盖总是保持高度精明。他不想让他的演员为了广角镜头和主镜头之类的东西演得精疲力尽。所以,他会拍摄他认为所需的让观众进入和抽离各场景的素材。然后他会花很多时间让演员找到他们的立足点和角色,从而给出他们的表演。
平均来说,他会拍4-6条,但他允许演员慢慢来,拍下最优秀的表演。当我们去到剪辑室,我们的任务就是尝试精简这些素材,让它们变得高效……加快它们的速度之类的。我们能得到很不错的原始素材,而我们的挑战通常是尝试让所有素材共同推进、顺畅衔接到一起。

他告诉我,你会在他位于奥马哈的家里做一段时间的剪辑,随后在你有更多时间进行后期制作时回到洛杉矶?
是的,我们会在那里待一个月,然后回到洛杉矶,再过去那边。我在那里剪辑了《公民露丝》和《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我很喜欢那里,我们度过了很快乐的时光。他的房子很不错。
在那里我们会用Jump Desktop做剪辑——我们会登录上去,在上面做所有的剪辑。这个平台很不错。它是最完美的工具。我们能从亚历山大位于奥马哈的家中剪辑加州电脑上的素材。随后,我们会用Evercast来与我们的同事——剪辑助理明迪和艾丽莎,音乐剪辑师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声音总监弗兰克·盖塔(Frank Gaeta)——开工作会议。整个过程高效轻松。
整个项目从拍摄到完成片大概是九个月。所以(项目周期)并不是太长。随后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月时间进行最终混音和数字中间片等工作。
《留校联盟》是亚历山大的第一部时代片,我很喜欢你在片中使用的叠化转场,这是在其他电影中很少见的。
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我们很喜欢这种技巧。它们看起来很漂亮。它们能营造情感,而我在还没和亚历山大合作前就很喜欢这种技巧了。我总是觉得它们太棒了,而我们一直在使用这种技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民露丝》。我们在《校园风云》(Election)和《关于施密特》中也做过一些长的叠化镜头。在《关于施密特》中,在主角妻子去世时有几个特别优美的叠化段落。在沃伦·施密特去世后,有一个长达两分钟的叠化段落。
最难剪辑的场景是什么?
有好几个。看起来它们好像很简单,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场景上。首先,是保罗最片尾被开除、为那个学生承担罪责的场景。我不会说我们很纠结,但我们一直在微调那个场景,倒回去将某些部分剪掉又加上某些东西,反复尝试将这个场景剪得恰到好处。这个场景花了我们挺长时间。
还有一些有点长的场景,需要精简一些才对。第一个场景是,玛丽和保罗在观看《The Newlywed Game》电视节目,这个场景的剪辑具有挑战性,因为我们剪掉了相当长的一段对话。这个场景比较有难度,因为包含很多内容。有她对于自己儿子的情感,还有对于学校里的孩子的气愤。还有很多不同的转场,以及角色方面的内容,在这个场景中剪辑是个挑战。

我猜测,你应该做了不少临时配乐吧?
是的。一直以来担任我们剪辑助理的明迪·埃利奥特(Mindy Elliott)这次倒是担任了副剪辑,她是第一个导入The Swingle Singers人声乐团音乐的人,也就是我们听到的阿卡贝拉版的圣诞歌曲。这个选择很棒,因为我在“聆听”电影中的任何音乐时都感觉不对。这成了我们接受的一个重要元素——全片都使用这种类型的音乐。
有时这会有点讽刺意味,也有点好笑,但在其他时候就令人心酸,并且这成了这部电影中的一大重要音乐元素。我们还和我们的音乐制作人/总监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合作,他的能力非常优秀。他也加入了许多音乐,包括马克·奥尔顿(Mark Orton)的配乐,我们曾和他在《内布拉斯加》(Nebraska)中合作过。这就成了我们在整部电影中添加的配乐。随后我们加入了我们所有那些有趣的60年代的音乐——这只是一个“自由放任”的举动。最后效果很好,但你会发现这需要花费10万美元(约72万人民币),而你无法拿到这么多资金。这种事是很常见的。
显然,《留校联盟》并不是那种视效密集型的大片,但还是有一些视效。你是否也在给这些视效做临时配乐?
我们有合成和流体变形之类的东西,但这部电影的视效全在于夜晚的雪景。有些特定的场景需要这种视效,例如当所有人都离开教堂时下雪的场景。无论你信不信,那个场景和所有男生被带到卡车前的场景是同一天拍摄的。那天早上是蓝天,后来疯狂下雪。几个小时之后又变成了蓝天。

Crafty Apes公司制作了所有的视效,添加雪,让道路看起来湿滑,给天空加云,有时添加几片雪花,尝试让画面看起来稍微更像那天早些时候拍摄的画面……这类的视效。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工作流,以及你使用的剪辑工具吧。
我们在Atlas Digital(即Runway Edit)公司提供的Avid Media Composer 2018上进行剪辑。在拍摄时,副剪辑明迪·埃利奥特、剪辑助理艾丽莎·多诺万·布朗宁(Alyssa Donovan-Browning)和我在家工作,我们以不同的项目文件来剪辑,并通过Dropbox保持更新。我们也有单独的硬盘。
我们的样片由伦敦和纽约的Harbor制作,每天早上——有时会在凌晨2点-6点间——他们会给我们发送一个可下载的链接。我会在凌晨4点左右检查我的邮箱,如果我收到了链接就会开始下载,然后再去睡觉。大概在早上8点,明迪会使用TeamViewer来登上我的电脑,并将整理好的样片媒体夹等文件复制到我的本地硬盘上。明迪和艾丽莎也有本地硬盘。我们会使用Telegram Messenger聊天功能保持联系,当我需要什么文件或收到新的媒体时(少量),我们会使用TeamViewer和Dropbox来下载和导入。
在亚历山大回来后,我们就会搬到北好莱坞的一家更传统的剪辑室,并换到一个跟我们剪辑室同在一栋大楼的Nexis共享媒体存储平台中。在我们最终完成剪辑后,就会永久搬到洛杉矶进行完成片制作,我们会在圣塔莫尼卡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混音师帕特里克·西科尼(Patrick Cyccone)一起进行混音。
你是否参与到了数字中间片(DI)的制作中?你是否有去进行DI审片?
在这个项目中我并没有太多参与DI制作,因为我们的摄影指导(DP)埃吉尔·布莱尔德(Eigil Bryld)在纽约拍摄,而亚历山大和埃吉尔在纽约的Harbor和调色师乔·高勒(Joe Gawler)一起制作了DI。我会观看它,当他们完成后,我会去到纽约,我们会进行试映。
是什么让你和亚历山大能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
我觉得是我们都是很随和的人,并且我们总是希望享受生活。我们会严肃对待工作,但从来不会让工作变成苦差事。我们在合作时总是很愉快,并且工作努力,但同时也保持着积极的态度。我猜,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很像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合作,我们已经成了好兄弟,所以当我们在合作时感觉甚至不像在工作了。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做好自己的工作,找到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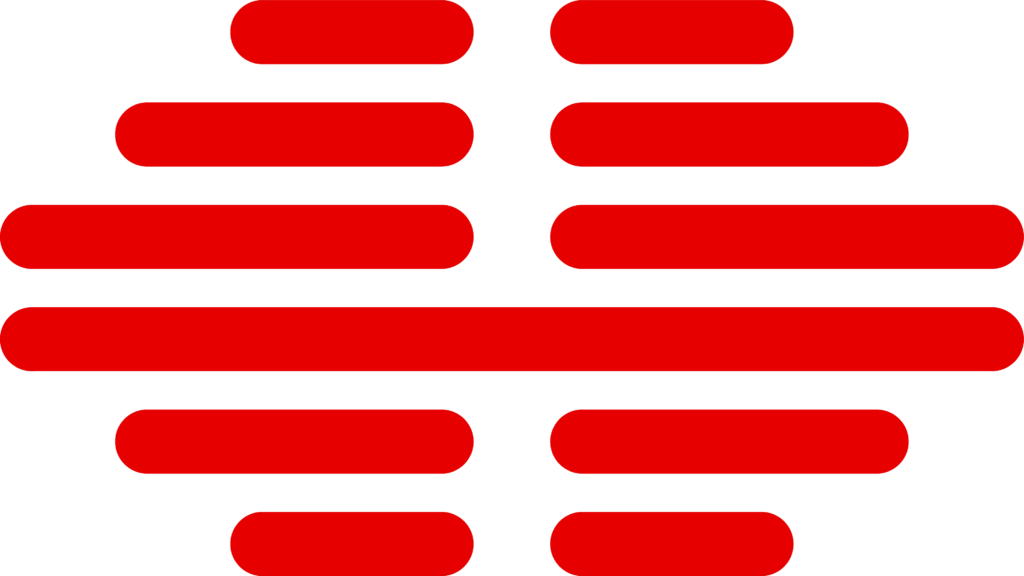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Iain Blair | postPerspective
翻译:Katja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