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有旻(Yoomin Lee,暂译)是伦敦Company 3分部的一名调色师。该公司是一家全球性公司,提供长片电影、分集电视节目、广告、游戏等多种形式内容的后期服务。“为各种项目——无论规模大小——工作的自由,是吸引后期人才为Company 3工作的主要因素。”李表示。
我们和李聊了聊,以了解更多她的工作方式和灵感来源。
作为一位调色师,这个头衔下最令人们惊讶的是什么?
当我说我是一位调色师时,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染发师(译者注:两种工作在英文中都是“colorist”),所以我这份工作真实存在这件事会让他们感到惊讶。
做项目时,你有时会被要求做调色以外的工作吗?
除了调色,有时我还要做一些合成。美颜、擦除和给图像增加一些纹理也常见于调色工作。我们的工具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它们完成很多工作。

你最近参与的项目有哪些?
为雅各布·萨顿(Jacob Sutton)的路易威登扬声器和耳机影片调色;为安东·寇班(Anton Corbijn)的长片电影《化圆为方》(Squaring the Circle)调色;为欧舒丹的全球宣传活动“礼赠的艺术”(Art of Gifting)视频调色,以及为由奥特姆·代·怀尔德(Autumn De Wilde)执导的2023年维特罗斯超市圣诞活动视频调色。
你喜欢怎样和摄影师/导演一起工作?
理想情况下,我喜欢与他们面对面一起工作,因为这能让我们建立关系和进行实时互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远程工作变得更加流行,也成了我们与电影制作者合作的又一种工具。
你喜欢摄影师或导演如何描述他们想要的风格?比如实际例子、某种可模仿的胶片,等等?
比起口头推荐,视觉参考能更好地帮助我理解客户需求的基础。从那里开始,我们可以一起打造这部作品。
一起工作几个项目后,事情会随时间流逝变得简单起来:你已经理解了他们的构想,也已经熟悉了他们的品味。
从调色的角度,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充分利用某个项目?
当客户清楚他们想要什么的时候,这总是有帮助的。然而,我认为在调色会议上留下一些探索的空间是好的。有时,我们会从客户那里得到逐镜头的参考资料,这可能会限制你的成果,因为在你看到不同或更好的效果之前,很难判断眼下的这个是否是最佳的方法。
你们是否提供片场使用的LUT?
有时会,如果有要求的话,但我们往往选择更通用而不极端的风格,所以对大多数镜头都适用。
在制作电影、分集电视或广告时,你的工作流是如何变化的?
对于长内容,我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来打造基础的整体效果,而不是逐镜头地过度精细化操作,而对于广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精细地调细节。
你用什么系统调色?
我同时使用FilmLight Baselight和Blackmagic达芬奇。
关于调色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是打造美丽的图像,为普通的图像赋予生机。没有哪两天的工作内容会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喜欢给图像带来生机。不过,我也喜欢这份工作的技术性和创意性并举。看到项目在调色后的转变令人非常心满意足。
直到开始在一家后期公司做初级工时,我才发现调色师这个职位的存在,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职位着了迷。
如果你不做这份工作,你会做什么?
我可能会成为一名建筑师。建筑物的形状和形式能讲述故事,而建筑物也能在视觉上令人愉悦。这和成为一名调色师其实原理上是相同的。

你最自豪的项目是什么?
为U2乐队《Joshua Tree》30周年音乐会打造视觉风格。参与这个项目,并看到视觉风格呈现在200英尺(约合61米)宽的屏幕上,而前面是传奇的U2乐队在全球39个城市巡演,这太有乐趣了。
你在哪里找灵感?艺术?屏幕摄影?Instagram?
任何地方!任何视觉性的内容都是我的灵感来源:平面摄影、绘画和电影。多年来,自我成为一名调色师起,我就在不断观察世界各地的光线在一天中不同时间的变化。
有没有哪部电影或电视节目能作为令人惊叹的色彩运用例子,让你印象格外深刻?
太多了,但最近我看了《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影片由欧格斯·兰斯莫斯(Yorgos Lanthimos)执导,由我在Company 3的同事格雷格·费雪(Greg Fisher)调色,看起来非常惊艳。
你能分享一些你日常离不开的技术吗?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我用我的手机拍下灵感来源的照片,并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渠道寻找灵感。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不在Instagram和社交媒体上花太多时间。
你如何从工作中释放压力?
我家里没有电视,主要是因为我害怕在家用显示器上看到我负责调色的内容看起来和我调的不一样。而我工作时一整天都会坐在监视器前,所以当我在家的时候,我会尽量避开和工作时一样的环境。我努力过着一种“模拟”(analog)式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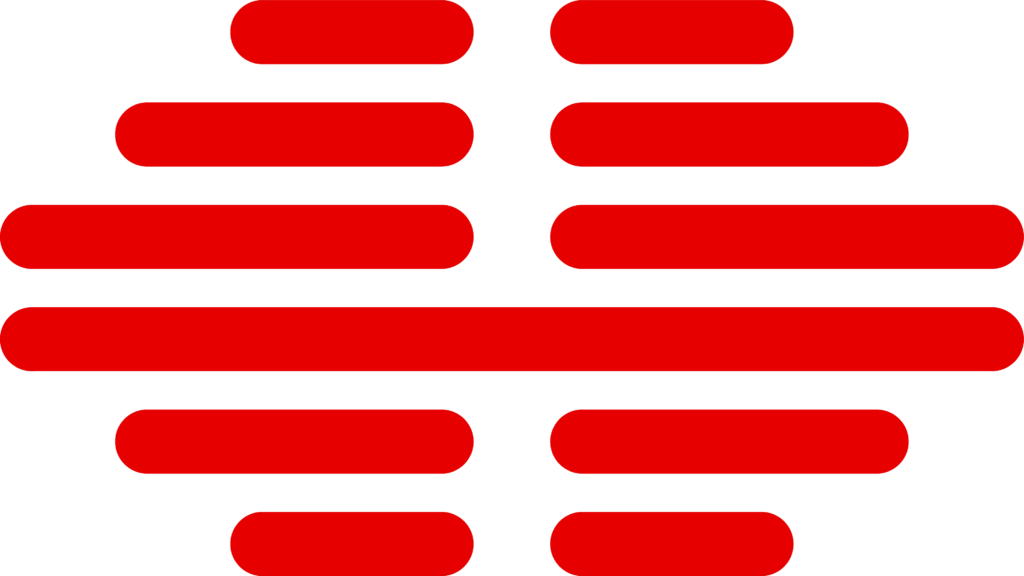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postPerspective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