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摄影指导(DP)不想被错当成是别人,但在我提到《五月十二月》(May December)最初找的DP是艾德·拉赫曼(Ed Lachman)这件事时,克里斯·布劳维特(Chris Blauvelt)对此毫不在意。这是个很容易犯的错误,除非你对他的作品足够了解:布劳维特取代了托德·海因斯(Todd Haynes)常合作的DP拉赫曼,后者因为受伤而无法负责这部新电影的拍摄。相应地,他负责拍摄的第一个外景镜头让我记起了他——那种大量而明显的颗粒感也出现在他与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合作的影片中,给人感觉深刻且自然。
布劳维特携《五月十二月》在今年五月的EnergaCAMERIMAGE电影节上亮相——几日后,该片将在全美上映,而两周后,该片也将在Netflix上线。在波兰托伦的哥白尼酒店见面时,我想问布劳维特的一系列问题被我们的对话盖过了,于是最终,本次采访涵盖了这部影片制作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后面信息量很大的一个部分:我试图以一种不那么常规的方式了解Netflix为影片带来的加成,而采访内容也表现出了布劳维特非常善良友好的性格。
The Film Stage:我之前都忘了是你拍的这部电影,入场去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艾德·拉赫曼的作品。
克里斯·布劳维特:是的,我正打算问你这个问题。没错,你可能以为会是艾德。
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夸张:第一个外景镜头出来我就记起这是你拍的了。我想:“这有那种凯莉·莱卡特很多作品里常见的噪点、颗粒。“
当然。
所以我突然想起:是克里斯·布劳维特拍了这个。
哇,能通过这种有质感的颗粒感影像被认出来,还蛮有趣的。
去年我看了《开展在即》(Showing Up),很喜欢……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形容它。因为那是数字拍摄的,所以……
对。我们加入真正的颗粒——真正的胶片颗粒。是我们后来加进去的;我们把它们添加到图像中以增加质感。
还有:我们俩都是胶片爱好者,所以我们的参考资料都来自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假面》《冬日之光》之类的电影。甚至《毕业生》也是我们的参考来源——构成了我们这部电影的喜剧元素。但是没错,这就好比:当参考材料来自胶片电影,我们也总是会想要那么拍。
这很有趣,因为艾德和海因斯合作的作品里这种质感并没有融合得那么彻底。那些作品自然也带有胶片式的风格——比如《黑水》(Dark Waters)是数字拍摄的……
没错。
……但他一直在上面额外加东西,让它看起来更像胶片。
是的。但你看,《卡罗尔》(Carol)就是16m胶片。而那就是我们喜欢的作品了;那看起来超级棒。
我想知道的是,影片用Arri Alexa数字拍摄,让这部电影带有这么强的颗粒感,这个决定多少是来自于你,以及多少是来自海因斯。
那种事在前期制作阶段就已经决定好了。还是那句话:它来自托德之前收集好并展示给我们的灵感来源参考材料。比如他会问:“这个怎么样,克里斯?”然后我们就去看环境,看拍摄地点——那套房子靠近水。那里的窗户会显示出一点海景,就像这部电影一样。我们当时希望能有这样的效果,让它看起来非常有层次感。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目标。所以等我开始测试镜头和摄影机……我们就选择了三十和四十年代制造的那种Kowa镜头,是吧?然后我用风格很强的滤镜,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追求一种质感方面低对比度的胶片效果,是吧?所以这部分马上就确定下来了。
关于镜头:我看过你们俩为《名利场》杂志做的那篇访谈文章,里面顺便提过一下这部分。我对此很好奇,我猜你有在暗示你的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整体而言,用这么旧的镜头拍摄的感觉怎么样?因为站在摄影技术的层面讲,这似乎也太过于古老了。
没错!我觉得找到这些我们以前用的古旧美丽镜头非常有意思,因为数字拍摄的效果可能会超级清晰锐利。
你瞧:如果你清晰且正对传感器地拍摄一切,极高的清晰度并不讨人喜欢。你现在看到的是皮肤上的毛孔,而这并不像过去那样有着“电影式的风格”,并不让我们所有人受到启发或喜爱。因此,有人一直在改装这些旧镜头,以匹配我们所有的设备,让它们更加趁手。其中有些这类镜头——比如你去看看它们外壳的内部——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原始镜头。
我昨晚刚和一些技术人员谈过——因为三十年代制造的Baltar镜头有这么件事:你不能随便把它们打开,因为它们是有毒的——会有有毒气体——因为它们已被封装了很长时间,它们使用某些材料,比如松焦油来让内部零件保持运作。所以技术人员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镜头包裹起来。就像改装过程其实只是在旧镜头的外部再加一层。于是你会看到一个这么大的镜头,有着对使用者友好的巨大对焦和光圈标记,而如果你往内部看,这镜头实际上才这么大。[双手比划]
当然。
而且这非常有趣。大概吧。这只是我们现在所处领域的一个有趣部分,我们已经采取了……人人都试图找到和挖出一堆旧镜头来平衡现有的高清晰度并让图像更平滑柔和。所以我在这部电影中使用了四十年代制造的镜头,我还加入了滤镜层和背光来制造炫光,让效果非常有胶片感。

过程顺利吗?还是说在某种程度上,镜头就只是镜头,而你只是……
不,这是个很好的观点。因为每款镜头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吧?比如,我们测试了Cooke Panchro;我们测试了Super Baltar、普通Baltar、Cooke S4——这是我会用的最现代的一款。但即便如此: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这些镜头都是三十五年前制造的(笑)。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能达到的锐度的上限了,因为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一种方法让我的眼睛不再为数字摄影过于完美的效果所困扰。
没错。当然。
但这有点像是:一旦拿到自己的工具包,你会去了解每种镜头和这些镜头的使用原理。镜头会有衰减,有时候我不得不让构图紧凑点因为有一丝自然出现的暗角效果。因此你必须在那个阶段学会理解和利用你的工具。但如果我要用的是一套新镜头,那所有东西都会现成在那里。这样的效果会更完美一点。而你可以接受这个事实。但在这些旧镜头套装中,你的50mm镜头可能会比其他镜头稍微偏冷一点。我的DIT肖恩·高勒(Sean Goller)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当50mm的镜头被拿来搭配摄影机时,他就已经在做调整了:他会在让图像偏暖一点。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我们选择的工具是什么。这是我们测试规则的一部分。
你说这些的方式相当细碎,比较带有自主性。所以我希望我下一个问题不会是个幼稚的傻问题,但是我真的想知道你有没有和海因斯谈过(或者交流过)他和拉赫曼的工作流程。他们在一起合作这么久,有时导演和DP很难分开。
没错。
拉赫曼的情况是他的股骨骨折了。我们实际上在戛纳采访了海因斯,他谈到了发生这件事时离拍摄只有几周了的情况。我想知道你是否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聊过这个过程,以及有多少方法能够复制出他们几十年来打造的这种风格。
是啊,不——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因为没人问过我这个。我的答案是:我和托德通话后打的下一个电话就是给艾德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或许已经做了多少准备工作。但他没有。他没有准备。他当时在拍另一部电影。结果他告诉我他在亚特兰大一家租赁商那里预留了一台摄影机,但是他说:“无论如何,你自由发挥吧。”于是我得到了传说级大佬的祝福。
他只是说:“自由发挥吧。”他说:“关于这部电影,我只和托德谈了一点点。”他那会儿甚至都还没开始准备,是吧?结果后来就差不多是我在发挥我的自由意志了——做自己想做的就行了。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得到了大师的祝福。他真的对我说了:“你得把这部电影拍成自己的作品,孩子。”我就感觉……像是骑士授勋仪式里,剑摆在了我肩头,然后我就觉得:“我天。”感觉像是另一种程度上让我战战兢兢。我心想:“哦,该死。我可得拿出真本事了。”[笑]
有种他会看着我的感觉。
对。是的,没错。
你和海因斯认识很久了——从你和格斯·范·桑特(Gus Van Sant)一合作那会就认识了,而他对你很友好,了解你的工作。我想知道你们俩曾有多希望未来某时能合作,而那些讨论是很明确,很公开,还是几乎像是种压抑的欲望似的。
有意思。你问的问题确实很好,因为我从不谈论这个。但在那种时刻挖掘一下自己的内心还是挺有趣的。我觉得我和托德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友好,而我们对彼此作品的喜爱、尊重和钦佩一直都在,因为他是凯莉(莱卡特)所有电影的制片人。他一直是她电影的一分子。他明确和我说过:“我真的很喜欢你的作品。”当而然,每次我见到托德,我都会觉得:”真不敢相信你刚拍的电影这么棒。你们都是英雄。”之类的。
但我从没想过:“天啊,我真想和托德一起去拍他的下一部电影。”因为:艾德。因为托德和艾德还在我心里,在我的梦境里。他们就像伯格曼和斯文·尼科维斯特(Sven Nykvist)似的。他们是传奇的梦幻组合。是吧?所以认识他们我就很高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不是那种会说:“我希望我能有这个机会”的人,我从没那样想过。所以这通电话,这通打过来的电话,也有点疯狂。我当时人在智利,在和与艾德一起合作了《伯爵》(El Conde)的灯光师一起工作。
噢。
所以当时我们整天都在聊艾德,而那位灯光师——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当然,艾德也是个非常贴心和杰出的电影制作者。之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我当时在拍摄地,不在通信服务区——是托德打来的,他说:“嘿。”他提到了一些关于艾德的事。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当时就想“哦,该死。”我以为艾德……你知道,我有不好的想法。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坐车开了大概两个小时才回到酒店打电话,然后他告诉了我实情。这太疯狂了,因为他在智利摔断了股骨,我当时就在那里,就在当地的一家酒店里。
这只是一种奇怪的巧合:我一整天都在和我的团队成员讨论艾德,结果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回到你的问题上,这超出了我的思考范围。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但是当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只觉得:“我天。”我挂了电话后给我妻子打了电话,我说:“你绝对不会相信的,艾德受伤了,他们谈了一下,决定:‘你来负责项目拍摄’。”(这是)如此光荣和疯狂的感觉,贯穿了我的身体和灵魂。
我记得当新闻出来的时候,说你会负责拍摄。我想一个相当普遍的反应是:“我希望艾德·拉赫曼尽快康复,希望他能尽快回到工作中,但如果要找其他人来拍摄的话,那就会是……”
对我来说太疯狂了。我还是对此有点冒名顶替综合症。我就觉得:“啥?很快就会有人把这一切从我身边夺走的。我不配。”是吧?所以听到这个,或者用这种方式去想,就感觉像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我知道也尊重我和凯莉还有其他人一起做过些值得留意的项目的事实,我只是作为一个心怀感恩的人坐在这里,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个荣誉。所以这有点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笑)对我来说。
海因斯和莱卡特之间有某些共同点——也许不是风格或主题方面的共同点——也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都是那种对其他电影给他们手头项目带来的灵感非常坦诚的导演。你在《名利场》杂志做的那篇《五月十二月》访谈文章就谈到了很多这样的内容。我很好奇:和这些狂热爱好电影的、会有大量参考作品的导演合作,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另外它们有没有影响和改变你自己的拍摄过程?
我觉得这得分两部分看。因为参考材料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好的,所以提供了很棒的工作起始点。由此我能理解导演们从中想要描绘的各种细微差别,这都是他们交给我的东西。托德给了我配乐。有很多特定部分他很讲究。“你瞧,这是我真正感兴趣想做的东西,而这是我的参考材料。”但是我不得不说,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自由自主地接受这些信息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而比方说在凯莉·莱卡特这边,我们会对镜头表非常严格。我们会就我写下的每一行字来回争论;我们也会就“不,因为什么什么我们不能如何如何”争个不休。这是非常健康且有趣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都是在为正确的理由把最好的部分精炼出来。
我们非常仔细地考虑了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们拍摄的是什么,我们对图像施加了什么影响,以及在某个时间点它对观众意味着什么。我们对这些事情都很谨慎。但凯莉会把这些统统抛弃。她可能会完全不想再看到定好的镜头表。所以整件事几乎就像是一次练习,目的是确保我们之间合作无间。我们现在已经练得好像有心灵感应了,知道什么拍法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但当我把镜头表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时,她会很讨厌我把它拿出来。但我还是会把它放在口袋里,因为我在上面写了关于dolly车轨道或者布光或者各种技术方面的笔记。
但有时我也会这样:“凯莉,我记了点笔记,我们该考虑一下这个。”然后她会说,“好啊,行。”然后我们就这么做了。所以这确实行得通。但我说这些是因为:是的,我们确实从别处获取灵感。是的,会有某种关注焦点。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是在试图创造一种电影语言来阐释他们的构想。
当然。
但这些灵感总会变成别的东西。创作总是自由的。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向世界敞开心态。就像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后实现创作自由。我不知道这么说有没有道理。
是啊。
你这是在很多层面上都用大量参考资料为自己做了准备,然后就可以看看怎么编排走位或者看演员做些什么,再说:“哇噢,现在我们要做这个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我也不知道——从一种奇怪的角度看,你是为了自由创作才做了那么多事。
你说的这些让我想到,在我观看他们的电影时——不管他们的DP是谁——他们创作时会感到一切都井然有序且强大有力,但不会很……封闭。因为有些电影会让每个镜头都显得非常紧张,让你有点喘不过气来。那些电影就不是那样的。
是的,我知道。这很有意思。我觉得确实有可能会做得太过火。人们很难让自己放弃控制:你肯定会想要手握控制。但我很幸运能和格斯·范·桑特一起工作,而他不会做镜头表。他连剧本都不喜欢。你可以和格斯在一个房间里编排走位,而他不喜欢周围有摄影机。“把它拿开。”他不希望任何人带有偏见,或被强加意见,或非要按照某种方向去表演。他就有那么固执己见。而对我来说,为格斯工作真的很难。我爱格斯。他是我的传奇人物、英雄和精神向导。他总是给我建议。但和他一起工作总是像在猜谜,他甚至不说正常的术语。比方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给你讲个故事。之后你在车里开车时,会想到:“现在我明白你之前想说什么了。”
但我觉得这是个人不会过度控制手头事情的例子。他并不是在过度强调或强加他的灵感或想法。但在和凯莉或者和托德一起工作时,他们非常聪明也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会制定计划。而这些计划永远提供开放解读,不过正因为有计划,拍摄时创作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象或构图了,因为我们已经想过要怎么拍——字面意思上的怎么计划就怎么拍。我们会仔细考虑我们要做什么。但我也说不好。这就像是:我们有一定的自由,但计划总是在那里当指引,而这两方面是实时一同运作的。因为演员们会带来别的东西,而托德很喜欢这点。他会觉得:“好啊,我们在这里展开一下。”这时你拍的内容就不完全符合原计划了。这很好——因为计划应该存在,因为计划是我们的保障——但也存在开放性可灵活变通。这就是会和我一起工作的电影制作者类型。

现在Netflix做了收购,你有没有和那边接触——比如给电影做杜比视界调色?
没有。我与Netflix合作过的唯一一件事……顺便一提,他们很不错。他们非常支持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我之前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瞧,Netflix是个大型集团公司,体量巨大。而且有一整个团队的人专门负责关照我们,支持我们和所有我们计划做的产出——比如上线流媒体。所以我们有为流媒体部分重新调过光,这是另一套过程了。
调光?
是的。我们放在数字画面中的颗粒没有转化成数字输出。所以我们必须回去再调,而阿德里安·斯利(Adrian Syree),我们的DI技术员,必须把颗粒加回流媒体版本中。这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多数时候,颗粒都会直接转化到别的版本,但因为这次加的颗粒相当重——我们给这部电影增加了相当多的纹理质感。而它没能直接转换到数字版本,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头再做这部分。而Netflix那边一直很好地支持这一点——比如为此支付费用,确保做出正确效果。还有,顺便说一句,我们要做一份这部片的胶片拷贝。
是吗。
在美国电影资料馆做。实打实在做这部分流程。我们拍了一部看起来像胶片的数字电影,而现在我们要把它做成胶片。这并不总是能前后连通。所以我们也得为此重新调光。
我不知道你能公开说多少。希望我不会冒犯到任何人,但我想知道能不能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他们希望颗粒减少这么多,但你又加入颗粒,因为你喜欢颗粒。那么中间的平衡状态是什么呢?
这部分我们是一起做的。托德和我看素材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哇,这样不行。”或者是中间转换的时候失掉了点什么。于是我们就又去找阿德里安,而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来给你们看些例子。”然后我们又重新做了一遍这部分。我们得找到正确的比例。
所以你也觉得它看起来有点奇怪吗?
是啊,很奇怪,感觉就像是,加了奇怪的刻意效果。
我之前就想问问35mm胶片拷贝的事了,你看过它了吗?
是的,我离开的前一天看了。它很漂亮。
很好,你对它很满意。
是的。是的。我是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它被转化出来。我们拿到了。我们找到了。
我和负责拍摄《杀手》(The Killer)的埃里克·梅塞施密特(Erik Messerschmidt)谈过——那部电影今年也上线了Netflix。他并不担心压缩或电视标准。而有些事情,你知道,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或大卫·林奇(David Lynch)会给放映员写信说:“这里该是这么多朗伯水平”和“你该把音量放这么大”。而上线流媒体有时就像打开动物园的大门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很好奇,作为拍摄这部电影的人,你是否担心有人在他们的电视上看这部片,然后比如他们开了运动平滑,或者他们……
哦,我的天。这是个必然存在在世上,而你只能放手随它去的噩梦。那会让我疯掉。是啊,我想都没法去想。因为没有底线。根本没有。你没法说:“每个人都会看到这种效果。”你所能做的就是在正确的领域尽你所能做到最好。就是这样。你得学会放手。就像是:“飞吧,小鸟。祝你好运”那样。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人用手机看电影,而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会生气。
因为他们通常不会告诉我。但这就是事实。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你努力在你最好的环境里做到最佳。我们可不会为最糟糕的那类观影习惯设计一部电影。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肯定会按最好的做;我们是在为影院放映做。
由此你会付出努力,让流媒体和离线内容还有高清电视看起来正确。但我不可能去每个人家里把高刷新模式关掉。但如果我想到这个,或者我去别人家里或者参加派对——结果电视开着这个模式——我见不得。我得离开现场。我没法去每一家影院在观众面前发表免责声明,尽管我很想这么做。是的,你不得不放手。那已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甚至在DCP之前,在放映机之前,一切也都是一样的——因为放映机各有不同,因为你的拷贝会正在世界各地流传,是吧?它总会在不同地方播放。还有声音。一切都各不一样。你控制不了。
哈里斯[萨维德斯]过去常常谈到这个,他会说:“我只得离开现场。”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能为这个影院做的最好的了。有次我在蒙大拿的一家剧院里,心想:“我的天啊。搞什么鬼?”就像那样。那里有个老人,一直不换放映机灯泡直到灯泡用坏为止。于是电影看起来就带有暗角——某种程度上这挺有趣的,因为这毕竟是台旧电影放映机之类的。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初衷,而你看得的是不同的效果。可你对此无能为力。顺便一提,即使是在片场,我们也是在高清环境中工作的——即使是不同的监视器看起来也是不同的。这种变动范围会让你发疯。如果我一直纠结于此,我会疯掉。
你家的观看设置是什么?一台特殊的电视机,还是投影仪?
我有一台投影仪。我有一台非常高端的很不错的投影仪。我们会把屏幕拉下来,而这是一个不同的领域。我真的很喜欢投影,而电视太特么锐利了,你说是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颗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用滤镜,还使事物更加柔化——以达到一种平衡。但还是那句话:就好像如果有人以高清那种完美观感看我的作品,我就会……呕吐,你明白吗?
我觉得这是一部优秀的面孔(visage)电影,面容——不只是因为出现的都是伟大的面容,但当然也有这个部分。那给人感觉就像是你看着那三位主角经历了几乎所有可能出现的情绪。
是的。
有趣的是你拍了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和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而我们得以看见她们极端的特写镜头——镜子,独白——还有查尔斯·梅尔顿(Charles Melton),我之前从未见过他。你真的可以在片中细看他们的脸。摩尔和波特曼经常出现在化妆品和护肤品广告中,因为她们差不多算是西方面容的化身。
是啊,她们就像是个品牌。你很了解她们。

我感兴趣的是你如何在利用熟悉感的同时,独特地拍摄她们。
是啊。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我的灯光师杰斯·韦恩(Jesse Wine)是第一个提到这件事的人。他说:“她们会带一个团队的人来,因为她们自己就是个品牌——就像她们在为任何化妆品牌拍摄一样。”美宝莲?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对流行文化就是这么不关心。但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了,而他说:“我们得确保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做她们要求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说:“天啊,真的吗?会发生这种事吗?”但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她们的团队来了,而那群人是很棒的电影人——他们很棒。他们给了我一些建议。比方说,有件事和朱丽安团队的一员苏珊(Susan)有关。她说:“嘿,你要知道:有时候,当DP看到她的时候,她是那种苍白的带点雀斑的姜黄色头发的外表,而人们会想趋近那种暖调来增强那种感觉,”她说,“这实际上不管用。”我说:“这是个好建议。”
我不想让她不好看。我只是想让她看起来活在现实中。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永远不要,呃……我对此很能随机应变的。我确实很尊重……女性在这个行业是如何被对待的。就好像,老有人说“老了就完了“。去他的。我讨厌这个。我觉得朱利安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之一。娜塔莉也是。我得有多幸运才能拍摄这些面容?还有查尔斯也是一样。
所以我从她们的团队那里学到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用偏暖的光给她布光,她很快就会变成“小橘人”。所以我不想这么做。于是我们在早期阶段就做了些测试,摸清楚了一套完整的比例体系。比如床上的夜戏:如果你用裸眼去看,那部分布景看起来是绿的。那里有绿光,而我以此来平衡洋红——那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由此我们建立了一套拍摄公式,非常酷炫——因为当我的调光师肖恩·高勒调掉绿色时,我们找到了针对她面部的完美风格。看起来很健康,很正常,很真实——她看起来很棒。所以无论如何:那句忠告是带有一点技术属性的——我得尊重演员面部,以这种方式拍摄。但除此之外——我只是把演员们当成他们的角色,只是想拍出这部电影。我说不好。我自己的大脑不会深入挖掘别人的个人历史。我只会觉得:“好吧,我们就是来这里一起做这个的。”我们都专注于这点。
差不多是《五月十二月》在纽约上映时,我看到海恩斯出现在标准收藏办公室,当时有一个Netflix-标准收藏联合发行交易。你觉得这部电影会在标准收藏发行吗?
希望如此。我对交易幕后一无所知,但我当然喜欢他们发行我的电影。因为,你知道,2006年时我已为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做了20年的摄影助理,而当时我告诉他我不想再为他工作,打算着手在自己担任DP上赌一把。这很可怕,因为我纠结于:我明明有工作,明明有生活,明明也很喜欢为哈里斯工作。直到今天,我仍然在思考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也就是从那次经历中获得了什么。而且即使是作为朋友……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是我的家人——我们从未断过联络。无论如何,当我告诉他我的想法时,他说:“抓住机会,放手去做吧。”
然后他说:“过来吧。”他住在公园附近,大概在108街和百老汇大街那边,而他对我说:“来我的古巴餐厅。我们一起吃早餐。”他真的太好了。我想:“他不介意这个。”他不是那种“你永远不能离开我”类型的人,而我们关系很铁。之前我们什么事都一起做,而我什么事都是跟他学的。他和我说:“你能上楼来看看我妻子,打个招呼吗?”之类之类的。很酷。我回:“当然可以。”然后就去了那里看了她,她的举止有点怪,我就想:“怎么回事?”然后她看向某处,那里有哈里斯给我买的全套标准收藏出版影碟——当时有700多部电影——上面还有个蝴蝶结。我哭了。那是他的……鼓励方式。所以对我来说,标准收藏不仅仅是……一个厂牌,是这个频道始终在线。那就是最好的。
这礼物跟送辆车或送艘船一样棒。甚至可能更好。
可能更好。
你从萨维德斯身上学到了什么?——去世十年后,他仍对现代电影有着影响。
学到了什么——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些问题,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我能告诉任何人关于哈里斯·萨维德斯其人其事的话,那就是:简洁、极简主义,以及真正的专注。那种真正的、诚实的对自己手艺的欣赏和专注。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是说,他也像个探险家——他是真的想“搞砸”一切。我们曝光胶片,烧掉胶片,在胶片上撒尿,烤胶片。我们尽一切努力寻求收获。所以,带着这些要素,你就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电影人。我真的相信这点。
我没去上过什么学。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去过少管所。我曾经是个人生过得一团糟的孩子,后来学到了我所学到的东西——优秀的职业道德——然后成为了一个真正专注于自己手艺的人,因为我欣赏电影:那就是我从哈里斯那里学到的。我意识到这个人会对我敞开心扉。他带我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也喜欢帮助别人。还有……我说不好。这也许是我能给出的关于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的最好评论。
如果任性的问题青少年能上一些为就业设计的电影摄影课程,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
同意!乔纳·希尔(Jonah Hill)和我在芝加哥为阿迪达斯做过一个活动,类似“电影人之日”之类的主题。他们带来了这些城里孩子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我们代表的是电影制作者,示范了一整套流程。其中有个孩子想当导演,而我们还有位服装设计师,一切就像是开了新大门:“剧组还有其他岗位也超级酷且值得尊重。”录音师把耳机给了这些孩子,他们都感叹:“哇,伙计。太神奇了。”在生活中领会这些很重要。我爸爸当了40多年的摄影大助,而他支撑起了一个家。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生活方式。他也不需要成为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他已经很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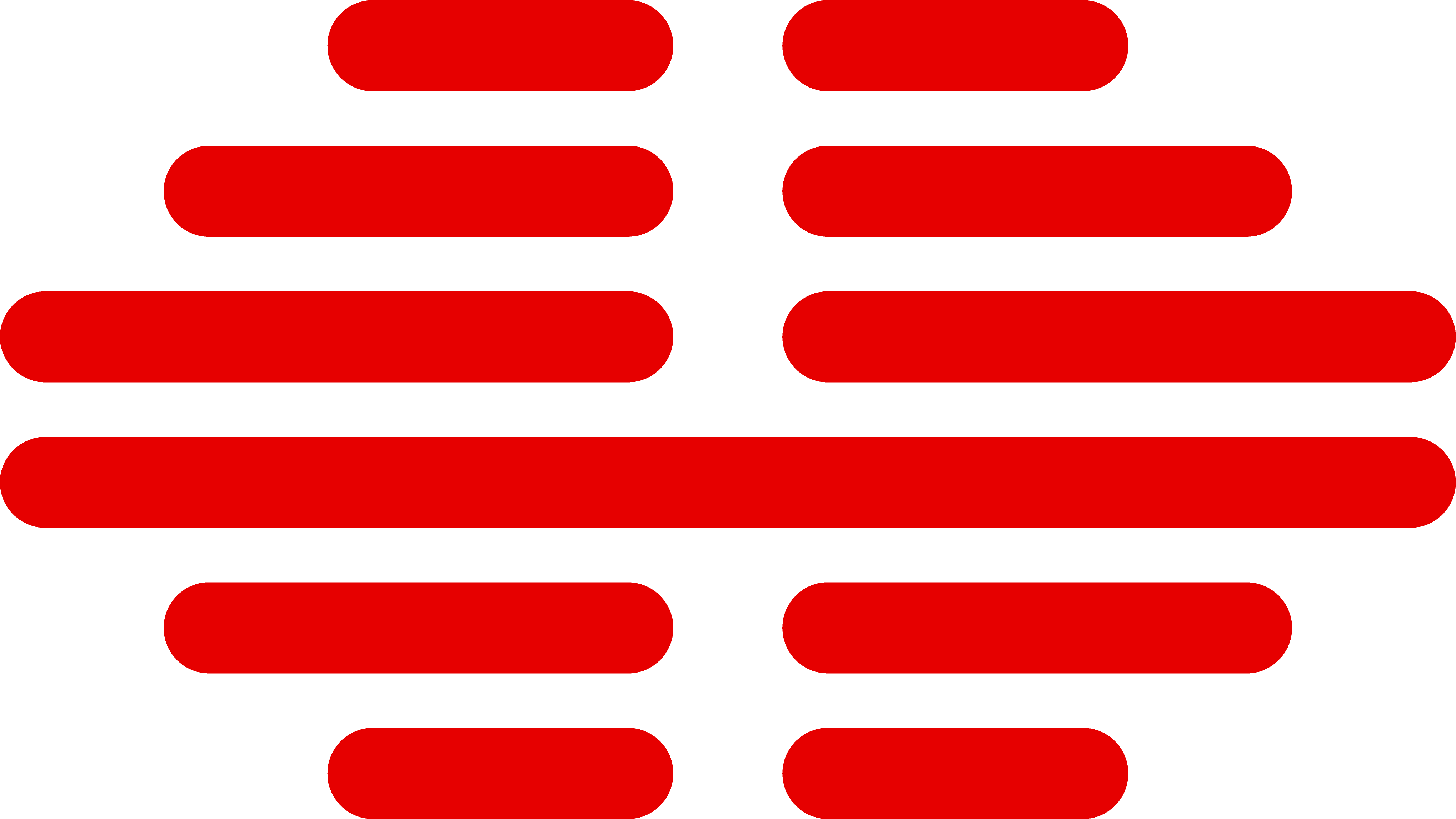
出处:Nick Newman | The Film Stage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