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罗·麦斯卡和弗兰基·科里奥在夏洛特·威尔斯的《晒后假日》中
音乐总监露西·布莱特(Lucy Bright)职业生涯早期在华纳古典公司工作,并为作曲家迈克尔·尼曼(Michael Nyman)担任经理人。2020年,她创办了自己的音乐出版公司Bright Notion Music——该公司与希尔迪·居兹纳多蒂尔、奥利弗·蔻茨和安妮·尼基婷等作曲家均有签约。她因《树荫》(The Arbor)和《西部慢调》(Slow West)等广受好评的英国电影以及更新近的《塔尔》(Tár)而闻名——在《塔尔》一片中,她对剧本中提到的作曲家的古典乐领域知识和个人熟悉程度,帮她创作出了这部被多个重要影评人协会评为最佳影片的电影。布莱特还凭借《晒后假日》(Aftersun)获得了英国独立电影奖有史以来第一个音乐总监奖。在该片中,她成功地将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Under Pressure》与奥利弗·寇茨(Oliver Coates)的氛围感原创配乐混合在一起,创造了近年来电影记忆中最令人难忘、最感人的结局之一。
Filmmaker:以前你曾在华纳古典公司工作,并担任作曲家迈克尔·尼曼的经纪人。你能告诉我你最后是怎么成为音乐总监的吗?
露西·布莱特:这两份工作是我最终成为音乐总监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一直喜欢原声和配乐,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实际操作角度它们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我觉得它们就像魔法一样。我在华纳古典时,我们签下了菲利普·格拉斯、史蒂夫·赖希和吉尔吉·利盖蒂,而我认为他们是这条路线上的三巨头。当我遇到菲利普时,我知道他是一位能够定义原声/配乐这种类型的作曲家,但我不认为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了他在电影世界的地位。这就是为《糖果人》(Candyman)写音乐的人!我开始思考这些联系:导演实际上会考虑他们具体想要谁来给电影配乐,然后他们会去请一位作曲家,而作曲家着手写音乐。我知道我现在大声说出这些的时候听起来很蠢,但这是从我意识到这个过程开始的。
我当时是华纳古典的公关,所以那会儿我在给利盖蒂的专辑做公关,而当我开始做研究和听他的音乐时,我意识到,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在《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或者《闪灵》(The Shining)中听到过。我当时没有意识到《2001:太空漫游》中(利盖蒂的《Atmosphères》)的这部分音乐并不是为了这部电影写的,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只是喜欢并想用它,而这背后有一整个故事——库布里克最初没有得到吉尔吉·利盖蒂(György Ligeti)的同意就拿授权用了这些音乐。其实事情比这个更复杂一些,但当我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棒。然后我开始意识到作曲家和导演之间发生的这种魔力,以及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我在华纳古典公司工作时认识了迈克尔·尼曼,因为我们发行了他的几张专辑。我之所以知道他的作品,是因为我喜欢《钢琴课》(The Piano),当然,但我仍然认为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电影的配乐,尤其是《绘图师的合约》(The Draughtsman’s Contract),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音乐之一。实际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很多音乐并不是写给电影,而是以前写好然后用进电影里的。由此我开始和迈克尔密切合作——他是一个性格很野的人,我们一起经历了一些货真价实的冒险。他让我做他的经纪人,于是我就离开了华纳古典来做这个。他被邀请给詹姆斯·马什(James Marsh)的《走钢丝的人》(Man On Wire)配乐,但当时他太忙了,没时间写新歌。但他为詹姆斯打开了他的旧作品目录,以此创作了新配乐——那是我第一次在剪辑室内看到这部分是如何运作的。我当时负责把音乐CD送到剪辑室,然后他们尝试做出各种新东西。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这个过程。约翰·博特伍德(John Boughtwood)是当时的音乐总监,而我和他既谈创意也谈生意方面的问题——比如我们怎么达成使用现成音乐的授权协议。我认为,(音乐总监)这个职位很有趣——它把我非常喜欢的两件事情结合在了一起。所以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这是个专门的职位,尤其是在(英格兰)这里。这部分在美国会更成熟,但这里只有少数人做这份工作,而约翰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离开去迈克尔(那边)工作时,约翰还是当时Music Sales的电影和电视部门负责人——Music Sales现在成了Wise音乐集团,然后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在那个团队工作。菲利普·格拉斯(Phillip Glass)的音乐当时由Wise出版,于是我回来与他和其他许多作曲家一起工作——一些人直接是电影作曲家,另一些则是碰巧也在电影界工作的作曲家。约翰算是指导我进入了音乐总监这个职位,而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到的。然后,一旦你做了这个职位,你就会开始和各路人物建立联系,会和同一个制片人或导演或剪辑师一起工作。但是没错,华纳和迈克尔是我走到那一步的关键人物。
Filmmaker:你一直都是个电影迷吗?你从小到大都爱看电影吗?
露西·布莱特:我确实是。我成长于八十年代,我认为那是电影史上伟大的十年。约翰·休斯(John Hughes)的电影《春天不是读书天》《早餐俱乐部》《红粉佳人》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这些影片的原声。我通过那些电影发现了很多音乐。现在几乎无法想象这种事了,但那时你只有去电影院才能看到电影,或者三年后电视上才会放某部电影,所以当时人们消费电影的方式非常不同——也许当时看电影更像是一种重要事件。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电影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几乎可以记得那十年我看过的每一部电影。不能看手机,看大银幕时不能看手机屏,只能全身心沉浸在电影里。如果我们要讨论音乐方面的话:我们为了让音乐听起来出众做了这么多工作,我们在混音中关注细微差别和进行细致工作,结果之后人们居然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看电影?我被路德维格·戈兰森(Ludwig Goranson)为《奥本海默》(Oppenheimer)写的配乐震惊了。它几乎是歌剧般的,从头到尾不间断地惊艳着我,是无比精心的制作。
Filmmaker:你能和我分享一些在音乐上很突出,启发了你,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影视剧作品吗?可以是你最近看的,也可以是你过去看的。
露西·布莱特:在原声方面,我觉得《熊家餐馆》(The Bear)很棒。毫无疑问,这是过去几年我在电视上看过的最喜欢的作品。我看了演职人员名单,看到了克里斯托弗·斯托勒(Christopher Storer)——剧集主创和制片,还是剧集的音乐总监,而这真的很有意义,因为一些音乐选择似乎对观众来说相当随机,但显然对他来说有意义,毕竟他已经创作这个故事相当一段时间了。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些歌曲选择的思考,以及这些歌曲显然对他个人有意义。
Filmmaker:你认为担任音乐总监改变了你和音乐的关系吗?
露西·布莱特:哦,我天,我可能已经成了你最不想一块儿看影视剧的人。我会一直对我的男朋友说:“我想知道这要花多少钱?”或者“他们怎么搞定这部分版权的?”控制住不这么想有点难,而且我敢肯定,这不是单单发生在我身上,也不会单单发生在做音乐总监的人身上。最近,我看了某部作品,其中有一首歌,我以前曾试图给别的作品申请使用过,但因为那个项目的性质而被拒绝了。我听到时就想:“哦,有趣的是,他们对这种用法没意见,但是对我们这种涉及‘性和毒品’作品的用法就完全不能接受。”
Filmmaker:有哪首音乐是获得了使用许可让你很自豪的吗?
露西·布莱特:好吧,有一首马上就要用上了,我不能说,但我对此真的很激动,因为这是一首我喜欢了有一段时间了的相当不知名的歌曲,而我很高兴我为它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使用位置。但更重要的是,导演也爱上了这首,现在已经无法想象没有它(来做这部电影会是什么样)了,这真的是我们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部分。很多人都谈论过这个,它已成为一种标志性时刻,但《晒后假日》有场戏用了《Under Pressure》。那完全是夏洛特·威尔斯(Charlotte Wells)自己的选择。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剪辑上,作(关于这场戏的)各种尝试,因为这场戏没按任何音乐拍。我实际上不知道他们在片场放什么让保罗跟着跳舞——甚至可能只是一点节拍。有时在片场,你只有一点节拍让大家去跟着跳舞,不一定会有一首歌。一切实际上都在剪辑中完成,夏洛特找到了它,并且效果很成功。但更重要的是,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通关挑战,部分原因是它太完美了。很难换成其它效果也能那么好的东西——不是不可能,但真的很难。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部片预算很少,而这是两位超知名艺术家合作的有史以来最知名的歌曲之一。所以,当你意识到为了得到使用权你必须面什么的时候,这有点令人紧张,而且我们没有直接使用这首歌——我们重新混录了它。
我们采用了主体,而奥利弗·蔻茨,这位了不起的作曲家,反复努力将其做成配乐。所以我们对此的要求很高,尤其是因为这是夏洛特第一次担任长片电影的编剧兼导演。保罗·麦斯卡之前出演过《正常人》(Normal People),并凭此拿下了一座英国电影学院奖,但他不是超级大明星,而且预算真的也没多少钱。这可不是那种上来就说“这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新电影”的情况。我们邀请了很多艺术家和组织参与,不过他们都很棒,而且他们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们把这个场景发给他们看——我对片方说得很清楚:我们就该这么做,而最糟糕的情况则是等(这部电影)上映后才出现什么我们没意料到的“惊喜”。显然,在你为一首歌获取使用权时,你总会给出一段场景描述,但对于这样的电影,这场戏是如此微妙,我觉得人们需要亲眼看到它,听到我们对这首歌做了什么改编。他们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就批准了。那可能是最让人伤脑筋的,因为你会想:“如果他们拒绝了,我们要怎么做?”但这也让我们非常满足感,而且我也很高兴它感动了这么多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会对这首歌有更深入的认知,至少这是我所希望的。
Filmmaker:我还很好奇,刚刚起步的年轻导演应该理解哪些使用授权音乐的要素?
露西·布莱特:我希望电影学院能教一下导演、制片人——实际上是所有从事电影制作的人——更多有关音乐版权和授权的知识,因为这真的很复杂。但是还有几件事——首先,实际上,你得为音乐预留适当的预算。即使是预算有一千万美元(约7200万人民币)的电影,你一参与进来,他们就会说:“呃,我们没有这么多音乐预算,我们只有一些会用在音乐上的应急开支。”如果这是一部音乐主要以配乐为主的时代片,而且可能会为片尾申请一首歌的使用权之类的,那还算合理。但这些是歌曲直接被写入剧本中的电影,且有着非常明显的场景,无论是在酒吧、夜总会,还是在车上的收音机里,必须配上音乐。
我说:“你为什么不留点钱做这个?”这基本就像是在说你没为你的调色或者你的音效混音留预算似的。这对我来说很有挫折感。还有就是,不妨对你的音乐总监为你解决音乐授权问题的结果心态更开放一点。比如你真的想用披头士的歌,但你肯定用不了披头士的歌,那咱们就一起想出点更有趣的替代方案。当然,尽管我很喜欢披头士乐队,但让我们想一些更剑走偏锋的方案或者选一首没有被使用过一百万次的歌曲。有时候我会感到沮丧,因为导演们会自带他们已经听了十年的歌曲列表,直到他们找到了拍电影的机会,而他们就是不会改变自己的音乐喜好。然后我也觉得他们没发挥出他们的音乐总监的最佳用处。
Filmmaker:你希望导演超级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还是希望他们把这部分控制权交给你?
露西·布莱特:有几位经常和我一起工作的导演是绝对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而这和我之前的回答不一样。比如西恩·麦德斯(Shane Meadows),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是个超级乐迷。也许他就像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那样,而你大概可以想象昆汀·塔伦蒂诺很可能完全清楚自己想用什么音乐,真的,他只是需要有人来帮他搞定版权。西恩和我就是这种关系。所以说真的,唯一有创意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得和艺术家们一起工作来理解他们对一首歌的构想。但是,西恩和我的品味非常接近,而且我们年龄相仿,所以我们的推荐的音乐往往非常相似——这或许就是我对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个事实感觉不那么冒犯的原因。还有一些和我合作过的导演是这样:我建议用某首他们不知道或者根本想不到要用的歌,然后我会看着他们爱上这首歌,这让我很兴奋。我认为有些导演比其他人更觉得音乐难以讨论,而这不是对他们的评判——任何人都可能觉得音乐很难讨论,因为这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很多情感都是如此。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帮助导演找到那些他们在听到前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想要的音乐,那真的很令人兴奋。
Filmmaker:能告诉我你想和哪些导演合作吗?
露西·布莱特:在我和他一起工作之前,我就已经公开表达过我想和西恩一起工作的愿望,现在我们真的合作了,这太好了。《铁爪》(The Iron Claw)是我和肖恩·德金(Sean Durkin)合作的第四个项目。我没有参与《双面玛莎》(Martha Marcy May Marlene),但之后的所有作品我们都是一起完成的。当你在合作者很年轻,或是在其职业生涯早期遇到对方,这种感觉真的很好——你们可以一起成长,培养出一种非常有默契的高效工作方式。我希望我现在和夏洛特·威尔斯就是这样,因为《晒后假日》优秀极了,而她将继续拍摄很多很多优秀的电影。所以也许我要找的是另一个在制作自己电影首作的人。这很个人,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列举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这样的电影人,她是一位很优秀的艺术家,但我肯定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这种工作关系。在别人职业生涯的中途加入挺有意思的。也许我答案里的那个人还没拍成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Filmmaker: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关于选歌的话题,但你是怎么为项目找到合适的作曲家呢?
露西·布莱特:那是我喜欢的部分。那很有趣,因为音乐总监并不总是参与配乐工作。有时这是因为导演和作曲家之间已经有了联系,而你不需要参与其中,交易也自然不需要经过你,而是在制片人和经纪人之间进行,然后作曲家和导演会直接对话,这很正常。但我非常喜欢参与这方面工作。你会想成为“媒人”,成为那个向他们提议某位创作者的人——然后对方爱上了你选的人并一起创造出了感觉只有那两人才能一起创造的作品。我对《晒后假日》的感觉就是这样。那是段有趣的关系,因为很明显,这是夏洛特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她以前拍过短片,但她那会儿还没有和作曲家合作过。
我们之前就知道她想要什么样的配乐,而且很显然,我不能只推荐一个人,但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奥利弗是合适的。这有一部分是基于个性,共同参考,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它重要的一部分。在夏洛特和奥利弗的第一次谈话之后,他马上写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直接用到了电影中。本质上那就是主题曲《One Without》,这基本就一锤定音了。然后在《生命不息》(Life After Life)中——这是一部尚未在美国上线的电视剧——导演约翰·克劳利(John Crowley)曾与不同的人合作过不同的项目,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他想要什么样的音乐的问题。我有种强烈预感沃尔克·贝特尔曼(Volker Bertelmann)会是个完美人选。而且,从他们第一次谈话开始两人就相处融洽。沃尔克创作出了很动听的配乐,而现在他们已经一起做到第三个项目了。能建立这种关系真是太好了。
Filmmaker:你通常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一个项目?
露西·布莱特:每个项目都不一样,但我会说,我越来越努力在剧本阶段就加入。有时候你只是在剪辑环节过来工作,这可能是在拍摄时不需要你提前为他们搞定版权音乐的情况下。但对我来说,更早加入项目会感觉更充实,这样你从一开始就可以着手创作音乐方案。比方说,我会根据演员的角色为他们制作播放列表,因为我知道这些歌曲不会以任何方式出现在作品中。但你可能会有种感觉,会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些音乐参考将会渗透到这个角色中,并且会对演员表演或对导演有所帮助。
Filmmaker:我注意到有很多女性音乐总监。
露西·布莱特:呃,我们可以谈谈女性作曲家的糟糕统计数据,它仍然糟糕得难以置信。但我不得不说,在所有项目的线下人才中,音乐总监性别比确实相对平衡。而且在顶层也很平衡,因为通常你会发现助理(层级)是平衡的,但顶层不是。我经常在想这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较晚出现的工种,因此——不像电影制作中的其他职位——男性掌权并没有百年的历史。因为这是个比较新的职位,所以从一开始它就能更平衡,因为它发展于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时期——当时我们终于明白,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是女人,就把她排除在一种职位之外。能实现这个挺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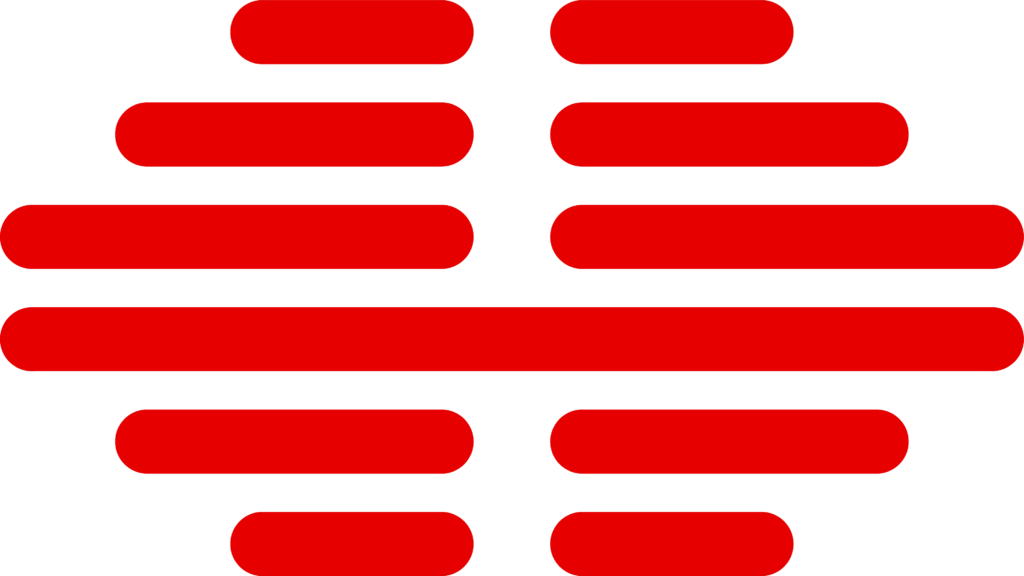
出处:Filmmaker Magazine
编译:Charlie | 盖雅翻译小组










-300x152.x33687.jpg)



